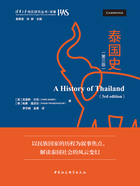
阿瑜陀耶的陷落
一语成谶,1767年,阿瑜陀耶城再次被来自阿瓦的缅甸军队围攻和洗劫。这次的破坏过于猛烈,以至于后来的历史著作将缅甸描绘成一个持续不断的侵略者,而抵御缅甸的攻击也成为泰国历史的核心主题。事实上,前一轮战争结束于16世纪晚期,它带来了一段安定时期:缅甸的影响集中在内陆地区,从阿瓦经过掸邦和兰那一直到澜沧和西双版纳地区;阿瑜陀耶则控制着从马来半岛的颈部向东到柬埔寨的海岸线一带。除了一些零星的小冲突外,暹罗和缅甸之间几乎有150年没有发生过冲突。
18世纪60年代的进攻并非古老主题下的最新篇章。相反,它们出人意料,非比寻常。它们源于一个新缅甸王朝向四方扩张其影响力的野心,并由重开控制马来半岛北部地区的竞争而引发。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缅甸这次野心勃勃,想要向东扩张势力,清除作为竞争对手的阿瑜陀耶王都。
缅甸的进攻是王朝间为了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又一场较量。但是经过之前150年相对和平的时期,阿瑜陀耶已成为一个更富裕、更复杂的社会。新的流行文化开始出现,包括谣曲、舞剧和其他主要在寺庙进行的表演形式。甚至连宫廷诗人也开始歌颂旅行的浪漫和性爱的欢悦,而不是战场上的胜利和关于王子的寓言。普通人也从依附的关系纽带中解放出来,不必卷入那种王室之间的战争,也不会被那种要求他们表现忠诚的思想束缚手脚。当缅甸军队抵近之时,阿瑜陀耶附近的许多人都通过贿赂官员逃避征兵。其他人则逃进森林,远离敌军的必经之地。王都向地方领主求援,却只有极少数人派出援兵。处于敌军进军路线上的城市,都集中力量进行自保,它们往往都通过投降来避免被摧毁。沿途的一些人被抓壮丁加入侵略军之中,另一些人则是为了获取战利品而加入。阿瑜陀耶的贵族们试图以他们用来制约君主制的佛教人文主义为基础,与进攻者进行谈判:“这就像大象打架一样。地上的植物和草都被压垮了……因此,请你的主君促使两国结盟,成为同一块黄金之地……两位国王都将因其使人民摆脱忧虑的仁慈而获得声望。”[12]
阿瑜陀耶的统治者明白,旧的尚武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弥补新兵的不足,他们垒高了城墙,拓宽了护城河,并购置了大量各式各样的枪支,当缅甸人打开军械库时,他们感到非常震惊。在这些防御措施的保护之下,城市还可以坚持一个战期,指望每年季风带来的洪水来解围。
但是缅甸人带来了三支部队,其总规模远超16世纪以来任何一支军队。他们在城外地势较高的寺庙周围安营扎寨,因此尽管有洪水,他们的围攻仍持续了两年多。城内的物资供应匮乏,许多人都溜走了。1767年4月7日,城墙被攻破。正如缅甸的编年史中所说,“之后,这座城市就被摧毁了”[13]。
缅甸人的目标不是要迫使阿瑜陀耶向它称臣纳贡,而是要彻底抹杀这个作为竞争对手的王都,不仅仅要摧毁该城的物质资源,还包括它的人力资源、思想资源和智力资源。任何能够带走的东西都被装车运往阿瓦,包括贵族、工匠艺人、佛像、书籍、武器,以及(据传闻)2000名王族成员。无法带走的资源都被摧毁了。城墙被夷为平地,军械库被捣毁。彰显王都和宗教中心的王宫和寺院都变成了“成堆的废墟和灰烬”。[14]
战斗断断续续持续了40年。阿瑜陀耶周围地区变得人烟稀少了。最初,缅军的主力进攻是通过兰那进行的,攫取人口、黄金和战备物资。后来,缅甸在1772年、1774年和1776年的进攻又重创兰那,以至于清迈被遗弃了,该城以北的大片区域都荒无人烟。1785—1786年,缅甸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五路大军共计100000多人,沿着北部兰那的山地地区,向南一直到半岛中部绵延上千千米,造成了大量破坏。彭世洛和其他北方城市也被遗弃。1802—1804年,兰那终于驱逐了缅甸人,但是清迈城缩小成了一个村镇的规模,其北边地区直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还未恢复定居。在南方,暹罗和缅甸的小规模冲突一直持续到1819年。1826年,第一位到访洛坤(Nakhon Si Thammarat)的西方人认为:“它似乎从未(从缅甸战争中)恢复过来”,只有“少数居民,没有贸易,资源微不足道”。[15]即使是中部平原的重镇叻丕(Ratchaburi),在1767年也付之一炬,直到1800年仍处于废弃状态,到19世纪80年代仍然有部分地区处于废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