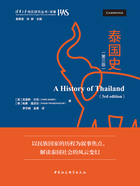
佛教与王权
上座部佛教(Theravada),即上座长老们的学说,与其他佛教派别不同,它将僧侣和寺院修行置于首要位置。僧伽或僧团的职责就是通过严格恪守戒律(winaya)或修行守则,去维护佛法(thamma)或佛陀的教导。一些僧侣研究经文,通过重抄来保存它们,并向俗众宣讲里面的内容。其他僧侣通过模仿佛陀本人的生活来体现教义,通过严格的苦行和冥想来获得洞见。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俗人的职责是通过赞助和保护来维持僧侣的生活。和其他地区一样,湄南河流域的民众对上座部佛教的狂热,主要是源于城市社会对其开放性和内在的平等主义的赞赏:所有人都有同等机会成为僧侣,为僧侣们提供赞助,并实现物质世界的终极解脱,即究竟涅槃(nibbhana)。
在实践中,这种纯粹的上座部佛教掺杂着其他宗教实践,包括印度教中的神祇、通常借自佛教密宗的超自然力量观念,以及民间对鬼神,尤其是预知未来和影响未来的力量的信仰。
东南亚地区的统治者青睐印度教神祇,因为它有机会将统治者和印度教万神殿中的强大神祇(毗湿奴、湿婆、因陀罗)关联起来,吴哥即是一例。因此,阿瑜陀耶的国王引入婆罗门来计划并执行王家仪式。但是印度教在暹罗并没有发展出本地信众。最常见的做法,是将印度教神祇改造成佛陀的侍者,或转化为地方的鬼神(正如他们经常在神庙中所做的那样)。因此,婆罗门教的王家仪式在宫廷以外意义有限。
统治者们也看到了将超自然力量混入佛教实践的机会。他们力图把自己和地方鬼神、神圣的佛像、圣山与圣河、白象、供奉于佛塔中的佛舍利和苦行的修道者的力量联系起来。但这些联系往往需要获得僧团的认可。因此,国王和僧伽就精神领袖和政治领导的相关角色进行协商。僧伽需要统治者所能提供的保护和赞助。作为回报,统治者可以要求对僧伽领导层的管理权力,以及僧侣对其统治的认可。作为回应,僧侣们可能会坚持要求统治者要治理有方,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利益方面都造福人民。在尚武的年代,僧侣们批评那些征税过重、在农忙时节征召民众、肆意抢占妇女或财产、杀生取乐、酗酒或树立不良榜样的统治者。一些重要的寺庙保留了评判每一位统治者的编年史,这些材料赞扬那些灵活地保卫城邦、以公正而慈悲的态度统治人民,当然还有供养僧伽的统治者。从这些微妙的协商中催生出法王(thammaracha)的观念,他是指根据佛法或佛教教义进行统治的统治者,以古印度的国王阿育王(Ashoka)为典范。在编年史中,这个观念被后世素可泰的统治者视为典范,他们使用达摩罗阇(Thammaracha,即法王之意)作为其王号。
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阿瑜陀耶的佛教热情高涨,这可能与贸易的增长和贵族阶层增强独立性有关。许多新的寺庙被兴建起来。维罕(Wihan,即精舍会堂)得到扩建,以便容纳更多的人。统治者们对其中一些项目进行了投资,但大多数项目来自贵族们的手笔。17世纪的国王对婆罗门教的扶持要多于佛教。纳莱王只修建或修缮了很少的佛寺,在佛教的庆典活动中也很少露面,他似乎对聚集在宫廷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青睐有加。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他质问道:“难道僧侣可以质疑国王?”在1688年的危机中,僧侣们组织人们拿起武器,阻止纳莱王的后代继续掌权。
在这次危机事件之后上台的国王并非王室宗族,而是一位一直在官僚贵族中备受欢迎的领袖。在这个新王统治下,阿瑜陀耶对婆罗门教的扶持减少了,与此同时,对僧伽的资助则大幅增加。波隆摩谷王(Borommakot,1733—1758年在位)及其贵族修建和修缮了大量寺庙,以至于阿瑜陀耶的天际线景致都完全改头换面了。他的个人虔诚非常突出,以至于获得了达摩罗阇的名号。他的声名远播,甚至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发源地斯里兰卡都派出僧侣使团,请求阿瑜陀耶的僧侣去帮助他们恢复已衰微的僧伽。
贵族们盛赞波隆摩谷,但也寻求更多的权力来制约君主。他们采用了《起世因本经》(Akanya Sutta),这是一部早期的佛经,讲述了君主制的由来,是对无序社会的恐惧迫使人们聚集起来“选出”最优秀的人成为王。贵族们在其对阿瑜陀耶后期的记载中称,每次王位更迭时,国王都是由贵族召开会议选出来的,但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愿望而非现实。贵族和僧侣们还强调,国王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是统治者的最佳人选,遵循十王道(thotsaphit ratchatham),即国王行为的10个法则,包括布施、守戒、捐献、正直、慈悲、自律、不瞋恚、不尚暴力、谦恭和秉持佛法。可能作于这个时代的诗歌作品《阿瑜陀耶预言长歌》(Long Song Prophecy for Ayutthaya),预言如果这些道德规则被忽视,城市将会衰落:[10]
若王不守十种王道,便生十六奇异苦厄
月星地空异动颠倒,四面八方意外遍生
巨云升腾有如劫烧,诸城乡村异象频发
……
阿瑜陀耶喜乐无边,胜过天堂数十万倍
将沦不义淫乱之都,不日沉沦呜呼哀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