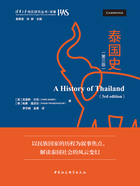
统治者与国家
在13—15世纪,战争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使得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可以扩张他们的领地。这场变革一部分源自火器的到来:首先是来自中国和阿拉伯的火炮,后来是来自葡萄牙的火枪和更好的火炮。但这场变革也源自对大象运输的更多利用,更高效的募兵手段,或者仅仅是由于风调雨顺养活了更多可供招募的人。
野心勃勃的统治者首先将临近的一些勐联合起来,结成联邦。在山地地区,各个邦(khwaen)都是由沿同一条河流相邻流域内的勐连在一起构成的。统治者经常派他的儿子或其他亲属去统治那些被征服的勐。统治者俘虏或吸引技艺高超的工匠们,把自己的勐打造得比其他勐更辉煌、更著名。统治者经常资助佛教,故而佛教在这个时代的城市中大受欢迎。佛教最早于公元5世纪来到湄南河流域,但其中夹杂着一系列印度神明,可能没有被明确界定为独立的教派和传统。在13世纪,僧侣们再次从锡兰带来了上座部佛教传统,根据宗教编年史的记载,它在民众的热情浪潮中像野火一样蔓延。统治者们赞助宏伟的佛寺建筑,尊崇以学识著称的僧侣,并收集佛陀的舍利和造像,这些都被视为精神力量的集中体现。
这些新兴的都城逐渐成为界定松散但是又显著可见的政治区域的中心。在湄南河水系的上游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清迈。它是在1296年正式建立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具有优越的猜亚普特征,由芒莱(Mangrai)建立,他可能是一位具有部分孟—高棉血统的傣泰人王子,他沿着滨河(Ping River)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邦国,并开始沿其他河流向东扩张,使当地的酋长们称臣。芒莱去世之后,变成了创建这个不断壮大的邦国的祖灵,在接下来近两个世纪里,之后的统治者都是从他的神圣世系中遴选出来的。清迈在这些继任者治下才真正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用壮美辉煌的寺庙装点了整个城市,并与东至难河(Nan River)、北至湄公河的酋长们结成了婚姻联盟网络。该地区被称为“兰那”(Lanna),意为百万稻田。再往东,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的法昂(Fa Ngum)家族沿着湄公河及其支流发展了澜沧国(Lanchang)。
在其南边,傣泰诸政权沿着山麓低地发展出另外一个联邦。起初,统治中心是素可泰(Sukhothai),传说中的立国先祖帕銮(Phra Ruang)的家族在此建立了一个辉煌灿烂的宗教都城。后来,中心和王族都转移到了彭世洛(Phitsanulok),可能因为这是个战争频发的年代,战略性成为一个比神圣性更重要的猜亚普因素。这一地区并没有获得一个独特的名字,只是被它的南方邻国称为“勐讷”(mueang nua)或意译为“北方之城”。
另一个联邦是由湄南河流域下游和海湾上部沿海一带的港口城市组成,尤其是四个11世纪左右在高棉的影响下建立或重建的地方:碧武里(佛丕)、素攀武里、华富里和阿瑜陀耶。经过这些地方统治家族之间的斗争,阿瑜陀耶在14世纪末成为统治中心。中国人称这个地区为暹(Xian),而葡萄牙语中则音变作Siam。[4]
这些统治中心都向自己周围的勐扩张影响力,但都以一种特殊的形式。附属国的统治者通常会被留在原地。他可能要送出一个女儿或姐妹做其宗主国国王的妻子,或者一个儿子去做服侍宗主国国王的随从;这些人都作为人质以确保附属国保持忠诚。在特殊情况下,宗主国国王可能会赐予附属国国王一个王族或贵族的妻子,她可以充当一个线人。附属国每年都需进贡,贡品通常是一些异域的或珍稀的物品。后来,进贡物品往往被标准化为银制或金制的工艺品树,这是马来人的创造。作为回馈,宗主国国王会赐予他们标识附属国统治者地位的徽章和仪式用品,或者赐予一些实用物品,如武器和行政体制。宗主国国王将保证保护附属城邦及其统治者免受外来威胁,而相应的,当宗主国国王需要调动军力时,附属城邦则承诺提供补给。但实际上,这些协议从来都不能保证兑现。
这些政治联盟的首要原则是确保附属国统治者不是被击垮,而是得到加强,这样他就可以成为更为稳定和有用的帮佣。附属的勐没有被破坏,而是被纳入一个更大的单位之中,从而增强了该单位的实力和光辉。统治者们夸耀的不是他们的疆域,而是依附于他们的统治者的数量。乔治·孔多米纳(Georges Condominas)称为“套盒”(emboxment)。通过这种原则,村庄被包含在一个勐内,而勐则隶属更高一级的勐,可能会向上经过多个级别。“曼荼罗”(mandala)、“裂变国家”(segmentary state)、“星云政体”(galactic polity)等术语被用来表示这种政治形式,但是“套盒”描述了其根本机制。
这种制度可能是在傣泰山地国家的世界中演化而来的,但是它的某些特征是从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借来的,该地区的沿海国家自公元3世纪以来一直参与其中。中国皇帝要求那些“蛮夷之邦”称臣纳贡,确认新统治者的继承权,并接受优越的中华文明的教导。作为回报,皇帝会授予其印玺,并承诺保护朝贡国。实际上,皇帝几乎没有派兵去惩戒某个抗命不遵的朝贡国,或保卫某个被围攻的朝贡国。但是“蛮夷”国家都遵命行事,因为朝贡地位可以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这是迄今最大的商品贸易需求来源。在此模式下,一些港口的勐与新兴的权力中心发展建立了朝贡关系,以获得进入其不断增长的市场的机会。那些权力中心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碑铭和编年史中列举了这些朝贡国,以炫耀自己远播的影响力。
这些军事和商业关系的网络是灵活多变的。中心不断崛起又衰落。在边缘地区,勐会同时与两个或更多权力中心建立平行关系,这些关系纽带的相对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波动。
从14世纪末开始,在湄南河流域及其周边出现的四大政治联盟(兰那、澜沧、勐讷、暹)开始相互对抗,开启了一个不时爆发战争的时代。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人们被迫加入大规模的征兵体系,军队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变得更加军事化,一种尚武精神盛行起来。强大的军队纵横驰骋,摧毁城市、抢夺人口、破坏庄稼,并引发传染疾病。但这些战争都不是决定性的。阿瑜陀耶的军队在15世纪末终于征服了清迈,但却徒然无功。这些中心可以摧毁对方并带走他们的人民、著名的佛像以及财富,但是远隔千山万水,他们无法将对方永远“套盒”。到16世纪末,这种战争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