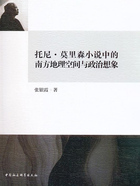
第一章 体验南方:身体实践与种族身份建构
历史上,身体被看作是一个斗争的场域,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福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监禁体系的研究,从身体被规训的历史中阐释了人的自由和本质的不可能性,从而强调了主体的建构性及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在后现代哲学这里,首先,作为物质的身体成为主体性建构的一个场域;其次,身体不再是本质的、非理性的,而是可写性的、可被塑造的实体,其自身具有充分的言说功能。“身体是自我规划的一部分,在这个自我规划当中,个体通过建构自己的身体来表达他们的个人情感需要。”[1]更进一步,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指出,身体作为劳动力的载体在生产、交换、消费等环节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斗争为例,说明了身体“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可以是一个积极的策略,但它也是政治抵抗的场所”[2]。身体实践与主体性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是指对身体整体或某个部分的“处置”,这种活动带有强烈的意图。这种身体实践包括被动和主动实践,前者的身体往往处于被压迫状态,由他人实施的一种实践;后者则是行为主体的选择,体现出其更强的主体性。
斯图亚特·霍尔在其1994年编著的《文化身份问题研究》一书的导言中对“谁需要身份”的问题做了两种回应。在第二个回应中他谈道:“关于政治,我指的是这个能指(身份)的政治运动的现代形式的意义以及它和地域政治的极为重要的关系——同时也指显而易见的困难和不稳定性,这显著地影响了‘身份政治’的所有当代形式。”[3]霍尔指出了身份与地域之间近乎天然的联系。同年,他的《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发表在论文合集《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上,后被介绍进中国。文章指出,身份并非是完结的,“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中”[4]。霍尔接着指出,关于文化身份,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自我:二是强调差异,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5]所以,文化身份具有稳定性、延续性和断裂性。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历史性,尤其是伴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文化身份会发生断裂,新的文化向量开始发生作用并促成另一种形态的身份生成。
正如大部分作家一样,莫里森的创作也是始于个人经验的。出版于1970年的《最蓝的眼睛》和1973年的《秀拉》都将叙事空间置于俄亥俄河沿岸的南部黑人聚居区里。尽管这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南部,但大量北迁黑人造成了黑人文化在此处的延伸。1977年出版的《所罗门之歌》实现了空间描写的结构化,北迁主人公通过南归获得了完整自我并实现了社会身份的追求。无论是《秀拉》中的叛逆女性秀拉,还是《所罗门之歌》中的男性黑人青年奶娃,他们都经历了促成个人主体性建构或者种族身份转变的标志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发生的场所基本上都是在美国南方乡村,它们被塑造为典型的黑人文化存留地,主人公们在此处的个体体验是其成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