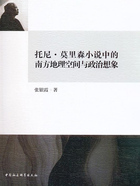
三 理论基础与研究路径
1.理论基础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空间与地方》中从经验的视角对“空间”和“地方”进行了研究。他说:“在西方世界,空间往往是自由的象征。空间是敞开的,它表明了未来,并欢迎付诸行动……开放的空间既没有人们走过的道路,又没有路标。它不存在已经成型的、具有人类意义的固定模式,而是像一张可以任意书写的白纸。封闭的人性化的空间便是地方。与空间相比,地方是一个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人类既需要空间,又需要地方。人类的生活是在安稳与冒险之间和依恋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运动。”[35]空间和地方既相互交叉又有所区别,被赋予了价值的空间就是地方,人往往能够在地方获得意义感和安全感。在人地互动中,人类的欲望、经验和情感都被投射到地方上,制造了种种面貌不同的文化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地方超越了作为背景的人类活动场所,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的、复杂的文化载体。
基于人类历史经验,麦克·克朗在其《文学地理学》中就地理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做了深入论述。他谈道:“文化地理学具有两层意思:一是文化利用地理使特定空间被赋予特定意义;二是这些文化的地理分布。”[36]他在对英国园林景观与权力和排外性、中国皇家景观和政治权力以及印度尼西亚通过地理景观将空间民族化的几个实例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是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以解读的‘文本’,它们能告诉居民及读者有关某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它们不是永恒不变的,也并非不可言喻,其中某些部分是无可争议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有些则含有政治意义。”“解读某一地理景观并不是发现某个典型的‘文化区’,而是研究和发现为什么地理景观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以及它们的意义是怎样改变的又是如何被争论的。”[37]
麦克·克朗提到了“双重编码”的现象,认为地理景观经常被另外一种表征形式包裹,文学、电视或者绘画都是这种表征形式的范畴。关于文学中“主观”的地区感受和人们对地区的理解,克朗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了文学中的地理景观和现象。
第一,人与地理之间充满了感染力和激情的关系。文学作品首先会描绘地理景观。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展现了充满情感的地理空间实践,因而对地理景观的描述往往被认为是带有“主观性”的。然而,这种看似非真实的描述其实更具真实性。克朗援引波科克的观点:“小说中的真实是一种超越简单事实的真实。这种真实可能超越或者是包含了比日常生活所体现的更多的真实。”[38]有关地区的写作,作家们对地理空间的描述首先建立在“对地区意识的理解”的基础上,如劳伦斯对诺丁汉矿区的描述,透过小镇里阶层团结的景象和乡下的自由景象展现了工人阶层的生活。部分文学中乡村景观预示了社会的某种衰退,如《德伯家的苔丝》中地理景观的描写揭示了金钱对土地的控制力,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诗歌则显示了田园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衰败。文学作品也塑造景观。作家通过对具有情感投射的地理空间的描述,塑造了现实生活中的景观,如英国湖区因华兹华斯的描述而闻名,许多人去那里感受他所描述的美。原本没有意义的自然地理景观被赋予了一定的审美特质,因而也构成了现实景观的文化意义。“描写地区体验的文学意义以及描写地区意义的文学体验均是文化生成和消亡过程的一部分……它们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39]斯瑞夫特的论述被用于解释文学创作的历史性特性,其中的地理空间也是有具体的历史语境的,并且这种历史感也造成了题材和体裁及审美风格的变化。
第二,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地理,而且作品自身的结构对社会结构也作了阐释。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人与空间和流动性的关系?作品如何赋予空间关系不同的意义?首先,家与外面世界体现了空间描写的结构化。创造家或故乡的感觉是写作中一个纯地理的建构。西方经典作品中对家的构建都是通过空间结构来实现的,如奥德赛、俄狄浦斯们对家的向往和追求一定是通过离开家到再次回到家这样的空间结构来实现的。其次,地理空间也揭示了两性之间的关系。从古典作品到当代小说,流动性、自由、家和欲望之间转变的关系说明了一个非常男性的世界。包括奥德赛、凯鲁亚克诗集中的流浪主人公们的行为都揭示出空间的性别范畴,两性通过地理表达出各自的欲求。这说明了地理体验(the experience)与自我(personal identity)之间的紧密关联。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社会价值与意识形态是借助包含道德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地理范畴来发挥影响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地理空间的结构,以及其中的关系是如何规范社会行为的。这样的关系不仅体现在某一地区或某一地域的层面上,也体现在家庭内外之间,禁止的和容许的行为之间,以及合法的与违法的行为之间”[40]。
第三,文学作品的“主观性”言及了地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文学描述城市和城市景观的意义是什么?克朗认为,城市空间和景观揭示了一种深刻的权利关系。雨果将贫民区与城市外表的规划与建设进行对照性描写揭示了一种知识地理即政府对潜在威胁的了解和掌握,同时也揭示了政府权力的地理。侦探小说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知识、性别与经济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对城市生活的描写,可以建构起现代生活的情感结构。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也经历了城市生活空间的转变,“流浪汉”与一些作家的自身经历非常相似,如福楼拜和波德莱尔。这些相似点更多地体现在写作的风格和对城市的描写中。“文学作品中对空间和时间的处理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城市地理空间开始碎片化,随着城市生活的节奏加快,时间似乎也在加速,人们感到了20世纪的来临。”[41]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的写作都昭示了这种变化,并带来了文体上的革新。
文学中的地理空间或者地理景观不仅是艾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中的环境,它更是一种主观情感和体验的表达方式。作家通过艺术手段将个体经验及欲望融合进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理空间中,从而建构出一个想象的、艺术的基于某个具体空间的地方,用以传达他对生存之境的态度与政治意图。美国斯坦福大学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retti)的《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是一部从地理角度关注文学的著作。书中第一部分介绍了文学中的地理。莫雷蒂谈到了地理对文学的作用:“地理不是一个惰性容器,不是一个文化历史‘发生’的盒子,而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渗透文学领域,并深入地塑造了文学,使地理和文学形态之间具有了深度关联。”[42]接着,作者辨析了文学中的空间和空间中的文学:“在第一种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个虚构的空间:巴尔扎克版本中的巴黎,殖民浪漫主义目光下的非洲,奥斯丁的英国重构等。在第二种情况下,它是真正的历史空间: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省图书馆,或唐·吉诃德和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生活空间。”根据莫雷蒂教授对文学地理的两种模式的划分,我们认为,文学中的空间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空间的虚构性。文学中的空间即文学作品中呈现的空间,它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空间。二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是建构的。在文学地理空间被塑造的过程中,作家不仅仅对非实存性地理空间进行描述,而是创造性地塑造,这个过程隐含了作家介入地理空间的角度、目的和立场,等等。
文学不仅仅是反映世界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本身更是一种社会的历史性表征。同样,“文学作品中的地理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它是一个社会媒体,人民的意识和信仰创造了这些作品,反之也被它们影响,作家们也不例外。文学作品的存在影响了作家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方式。文学作品不是一面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这些复杂意义的一部分”[43]。
莫里森在其小说作品中反复涉及南方乡村或者城镇,这是她写作的一个支点,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获得进入莫里森诗学世界的一重门径。莫里森笔下的南方乡村世界大都坐落在远离经济政治中心的僻远角落,与现代世界间或发生交流和沟通,显得闭塞与疏离,群体社会的自足性质比较突出,基于地域和种族的民族文化也生生不息,异常鲜活。但这些“小世界”或“地方”又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们整体地被卷入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急遽发展的工业入侵和族群间的交流与融合改变了最早的乌托邦式的群居形态,使得传统南方黑人村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事物,原有的单一文化面貌被打破并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在以南方村落和小镇为代表的地方与全球空间的错综复杂的互动中,我们可以从文本中看到莫里森对地方与世界关系的态度,感受到莫里森对民族文化与身份的固守、纠结与改变,以及文本传递出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重重张力。
莫里森的南方地理空间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想象的地理”。她本人出生在俄亥俄州,自称为“一个中西部人”,但她在一次访谈中谈道:“最近,我开始把我写的东西称作乡村文学,即真正为乡村、为部落写的小说。”[44]这个访谈是在80年代末,也就是在作者完成了第四部小说《柏油娃娃》之后。然而,这个时候莫里森的父辈早已逃离了南方,作为离开南地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黑人,莫里森实际上脱离了大部分“人民”生活的南方,远离了该群体生活的日常。尽管如此,莫里森还是生活在由黑人群体构成的社区当中,并从父辈和伙伴们的生活中感知和了解了黑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包括黑人民间歌谣、传说和民间故事等。与此同时,莫里森早期着迷于西方古典文学及现代派文学,硕士论文研究的是福克纳和伍尔夫。毕业后曾到得克萨斯南方大学和霍华德大学任教。这段工作经历使莫里森深入到南方,和自己的“人民”有了更深的接触,逐渐促成了莫里森创作的走向。所以,莫里森说:“我意识到(黑人的价值)直到很晚才清晰,我想,因为我离开家……去上学,我所学的东西是西方的,而且你知道,我当时对这一切都很着迷,那时来自任何我自己家人、亲戚的信息对我来说仿佛都很粗俗、愚昧。”[45]1966年,她在纽约兰登书屋任高级编辑期间编辑了《黑人之书》,该书记叙了美国黑人三百年的历史,被誉为美国黑人历史的百科全书。这段工作经历加深了莫里森对美国南方历史的了解。尽管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知历程,莫里森最初对黑人文化传统的记忆和实践以及后来的认识,都被作家珍视并作为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被保留,最终呈现在其文学世界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莫里森笔下的“南方”是一种想象的“南方”,是建构起来的南方。
2.研究路径
雅克·朗西埃在《文学的政治》中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在作为集体实践形式的政治和作为写作艺术制度的文学之间,存在一种特殊联系。他通过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创作验证了这个假设,揭示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其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它对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在谈到具体创作时,朗西埃说:“作家们必须与意指过程(significations)打交道。他们把词语当作交际工具来使用,而且不管是否情愿,他们借此介入建构一个共同世界的任务。”“文学是识别写作艺术的新制度。一种艺术的识别制度是一个关系体系,是实践、实践的可见性形式和可理解性方式之间的关系体系。因此,这是对感性的分割进行干预的某种方式,而这种分割确定着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世界对我们来说可见的方法,这种可见让人评说的方法,还有由此表现出的各种能力和无能。”[46]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包括语言、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在内的复杂时代环境的影响,他会不自觉地遵循写作艺术制度的内在逻辑,进而生产出与时代精神相吻合的文学作品。
莫里森把她的作品描述为“一幅文学批评地图……旨在开辟更多空间,有新发现,进行知识冒险和探索”[47]。可以说,南方地理空间叙事是探究作家知识冒险的一个恰切视角,它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她的文学探险路径。莫里森关于南方地理空间叙事的逻辑起点是作家的“北方”站位,小说人物与“南方”发生关联,叙述者在人物自身和他者之间来回变换,视角也随之切换。基于此,其文学作品大致构成了一条环形路线,从“体验”开始,到“回忆”历史、“超越”叙事,以及最后的“回归”南方。本书在安排这几个主题时大致与作家创作的时间顺序相吻合,当然,这样的编排从根本上是由于历史赋予文学创作的内在逻辑和面向。同时,这样的编排也清晰地呈现了作家的思想轨迹和文化立场。
论著的第一章主要关注南方与女性的身体实践及黑人青年的文化身份建构,着重强调了人物对南部地理空间的“体验”,这种体验与主体性建构和文化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留下的遗产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生活,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的观念开始被大多数白人接受,少数族裔和女性也用自己的行动迎来了新的局面。无数少数种族成员开始跻身主流社会,包括白人妇女在内的所有女性,她们的地位和权力也得到了历史性改变。受到时代精神的鼓舞,莫里森以文学创作呼应并延续了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核心议题。出版于1973年的《秀拉》强调了黑人女性的独立,作品中鲜明地突出了人物的身体实践,这种身体实践成为界域化南方空间“梅德林”的女性建构其主体性的一种主要方式。与此同时,1977年的《所罗门之歌》塑造了典型的非洲与美洲在场的共生体——南方小镇沙理玛。生活在北方的民族文化缺失的黑人青年通过南归破译了家族秘密,同时在了解了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后走向认同,进而完成了自我重塑。
第二章探究了南方地理、黑人群体的历史与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产生了一场由传统自由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经济危机,人口和资源开始向南部和西部的保守派大本营迁移,保守主义思想逐渐隆盛。与此种历史状况同步,莫里森的创作开始进入历史小说的写作阶段。回溯历史的常见手段之一就是回忆,时间的穿梭与变换成为小说连接历史与现在的主要方式。《宠儿》通过种植园奴隶的记忆回顾了他们在南部种植园的遭遇,而奴隶制的后果持续地影响着获得解放的黑人奴隶,鬼魅以其特有的时空穿梭能力把历史和当下连接起来。仪式是黑人奴隶疗治伤痛的方式之一,但其自我解放还是有赖于对奴隶制记忆的回顾与反思,并最终达致心灵自由。《天堂》再现了美国南部重建时期黑人建立家园的历史,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他们对家园的基本政治诉求,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南方地理空间建设实际上代表了他们的种种乌托邦实践。
第三章主要关注的是全球化时代流散群体的命运。20世纪末,全球化现象和民族主义勃兴的背后是经济繁荣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宽松,这造成了政治及文化的多元化面貌,文学创作题材进一步拓展。莫里森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黑人流散群体的文学叙事分别在美国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2008年左右。1981年出版的《柏油娃娃》提供了包括南方乡村在内的多重地理空间,主人公经历了文化身份错位、重塑及被否定,最终选择前往欧洲和流于身份漫游,这是与全球化时代地域和身份流动相吻合的一种历史状况。与近年状况相呼应,2008年在奥巴马就职前出版的《恩惠》的叙事时间则回到了美洲被殖民时期,位于美国南部的弗吉尼亚地区出现了多种族景观,同时进入了种族主义快速生产和传播时期。作品艺术地呈现了欧洲白人移民、本土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奴隶身份转变的历史面貌,以及种族主义从无到有的历史进程。尽管叙事地点都涉及美国南方乡村,但讨论的重点已经超越了地域本身的突出意义而进入一个更宏大的议题,即洲际人口迁徙及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
在第四章,论著把地理空间叙事置于现代性视野之下,讨论了现代化语境下南方地理空间的意义。奥巴马卸任之后,经济持续低迷使得保守主义潮流再次在美国抬头,整个社会呈现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倾向。保守主义者们表达了维护传统价值观、反对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及移民等基本诉求。莫里森2012年和2015年出版的《家》和《孩子的愤怒》都在叙事上回避了美国社会的尖锐问题,风格转向缓和、保守。1992年出版的《爵士乐》考察了北方都市、南方乡村及黑人艺术之间的关系,黑人移民如何处理南部经验与北方生活之间的矛盾,以及基于黑人布鲁斯的、融合了多元文化在内的爵士乐对都市黑人的意义。对《家》的研究主要是从现代性危机出发的,小说中备受战争创伤和种族歧视的黑人青年通过南归获得了文化救赎。无论是《爵士乐》中城市黑人对南方故地的回望,还是《家》中的“返乡”,两部作品都再次明显地突出了美国南方作为黑人文化集中存留之处的重要意义。这个鲜明的主题可以说是作家对早期创作的一种回归,且这种回归带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性意义,可以被认为是作家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是知识分子为此开出的文化“药方”。
从“体验”南方到最后“超越”和“回归”南方,莫里森历史性地考察了黑人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我主体性建构、身份认同、奴隶制遗产处理、理想家园的塑造历程,同时把视野投向都市黑人群体的生活状况,探究北方都市与南部乡村及黑人艺术之间的关系,试图为当代黑人的精神困境寻找出路。莫里森对自己的写作对象及人物活动的地理空间分布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柏油娃娃》出版后她就表达了这种认识:“福克纳写的作品我想可以称作地方文学,但全世界到处出版他的书。它优秀——具有世界性——因为它是专门关于一个独特世界的。这就是我希望做的事情。假如我想写一部具有世界性的小说,那会是水。在这个问题后面有一种暗示,即为黑人写作便是在降低作品的地位。从我的角度看,只有黑人。当我说‘人们’时,我的意思便是黑人。许多黑人写的关于黑人的书都有这种所谓‘世界性’的负担。”[48]莫里森以福克纳的例子说明了其写作的基本素材与路径:居于南方及与南方有着密切关联的美国黑人生活。清晰而精准的定位都展现出莫里森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作家的民族情怀。
[1]James Cone,The Spirituals and the Bluess: An Interpretation,New York: Orbis Books,1992,p.105.
[2]Toni Morrison,Playing in the Dark,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2,p.17.
[3][美]詹姆斯·M.麦克弗森:《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陈文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0页。
[4][美]埃里克·方纳:《美国历史:理想与现实》,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14页。
[5]王玉括:《非裔美国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及其文化表征》,《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6]Angelyn Mitchell,“‘Sth,I Know That Woman': History,Gender,And the South in Toni Morrison'sJazz”,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Vol.31,No.2,1988.
[7]Charles Moore,“Southerness”,Perspecta,No.15,1975.
[8][美]詹姆斯·M.麦克弗森:《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陈文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5页。
[9][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
[10][美]詹姆斯·M.麦克弗森:《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陈文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2页。
[11]Emily Langer,“Toni Morrison: Nobel Laureate Who Transfigured American Literature,Dies at 88”,Washington Post,August 6,2019.
[12][美]托马斯·勒克莱尔:《“语言不能流汗”:托妮·莫里森访谈录》,少况译,《外国文学》1994年第1期。
[13]Toni Morrison,“Rootedness: The Ancestor as Foundation”,in Mari Evans,ed.,Black Women Writers1950-1980:A Critical Evaluation,New York: Anchor Press,1984,p.344.
[14][美]克劳奇:《评 〈爱娃〉》,转引自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15]王玉括:《莫里森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Linden Peach,ed.,Toni Morrison,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98,p.9.
[17]Missy Dehn Kubitschek,“Toni Morrison: A Critical Companion”,African American Review,Vol.35,No.2,2001.
[18]Carolyn M.Jones,“Southern Landscape as Psychic Landscape in Toni Morrison's Fiction”,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Vol.31,No.2,1998.
[19]Catherine Carr Lee,“The South in Toni Morrison'sSong of Solomon:Initiation,Healing,and Home”,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Vol.31,No.2,1998.
[20]Gloria Grant Roberson,The World of Toni Morrison: A Guide to Characters and Places in Her Novels,London: Greenwood Press,2003.
[21]Tessa Kate Roynon,Transforming America: Toni Morrison and Classical Tradition,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rwick,2006.
[22]Christopher J.Walsh,“Dark Legacy: Gothic Ruptures in Southern Literature”,Critical Insights: Southern Gothic Literature,No.4,2013.
[23]Oumar Ndongo,“Toni Morrison and Her Early Works: In Search of Africa”,Sciences Sociales et Humaines,Vol.9,No.2,2007.
[24]Herman Beavers,Geography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Cham: Palgrave Macmillan,2018.
[25]曾竹青:《〈所罗门之歌〉 中的记忆场所》,《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1期。
[26]王玉括:《非裔美国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及其文化表征》,《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27]曾利红、黎明:《南方哥特小说中的幽灵意象——兼评 〈押沙龙,押沙龙!〉和〈宠儿〉》,《当代外语研究》2015年第5期。
[28]高卫红、张旭华:《解析 〈宠儿〉 及其南方文学特征》,《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9]王秀梅:《历史记忆与现实世界的冲突——威廉·福克纳与托妮·莫里森的对比研究》,《山东外语教学》2009年第6期。
[30]日本学者久藤田认为莫里森的创作明显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并认为她是福克纳的后继者。参见Hisao Tanaka,“Modes of‘Different' Time in American Literature”,The Japa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Vol.15,2004。
[31]卢敏:《黑白之间:爱伦·坡的种族观》,《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32]Carolyn C.Denard,ed.,Toni Morrison: Conversations,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8,p.182.
[33]Robert Stepto,“‘Intimate Things in Place': 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The Massachusetts Review,Vol.18,No.3,1977.
[34]Jennifer Rae Greeson,Our South: Geographic Fantasy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 Literatur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2.
[35][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一个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
[36][英]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37][英]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38]D.Pocock,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转引自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39][英]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40][英]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2页。
[41][英]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42]Franco Morretti,Atlas of European Novel 1800-1900,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8,p.3.
[43][英]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44][美]托马斯·勒克莱尔:《“语言不能流汗”:托妮·莫里森访谈录》,少况译,《外国文学》1994年第1期。
[45]Danille Taylor-Guthrie,ed.,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Jackson: Un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p.173,174.
[46][法]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47]Toni Morrison,Playing in the Dark,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2,p.3.
[48][美]托马斯·勒克莱尔:《“语言不能流汗”:托妮·莫里森访谈录》,少况译,《外国文学》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