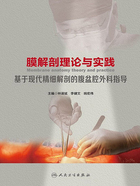
第三节 膜解剖理论的发展与展望
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及完整结肠系膜切除术在临床的广泛开展,促进了继器官解剖、血管解剖后的第三代外科解剖——膜解剖的兴起。膜解剖虽然掀起了热潮,但目前还是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要建立统一的膜解剖理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解剖名词不规范使用,比如全直肠系膜切除术临床已开展了20余年,但却存在脏、壁筋膜之间,脏筋膜前后两叶之间,直肠固有筋膜和泌尿生殖筋膜之间,直肠固有筋膜和腹下神经前筋膜之间等诸多“神圣平面”[10],其中有些实际上可能表达的是同一层面,只不过使用的是不同的解剖名词,比如笔者认为脏筋膜、泌尿生殖筋膜和腹下神经前筋膜是同一解剖结构(图1-8),TME的“神圣平面”实际上位于直肠固有筋膜和脏筋膜,而非传统的脏筋膜和壁筋膜之间[18],实际与Kinugasa[30]的观点是一致的:TME的层次位于腹下神经前筋膜(脏筋膜)和直肠固有筋膜之间。由此可见规范膜解剖名词对膜解剖学说发展的重要性。
人体解剖的名词中有关膜解剖的名词是最为混乱的,Terminologia Anatomica虽然经过了6版的更新,但有关解剖平面的术语并不在其收录范围,并且有些膜解剖名词实际是重名,比如耻骨尿道韧带虽然被文献广泛引用,但迄今也没有组织学的依据能够证实它是有别于盆筋膜腱弓的独立筋膜。更为重要的是,膜解剖的很多术语并不符合解剖学的定义,更多是出于解剖标记的需要来加以命名,这就很容易出现截取整体筋膜的一部分来命名的情况,比如妇科解剖中的盆腔悬吊系统,包括耻骨膀胱韧带、膀胱子宫韧带、直肠子宫韧带或宫骶韧带,实际上都是结直肠外科解剖中脏筋膜的一部分[18]。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膜解剖作为新兴的解剖学在传统解剖学中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传统的解剖学专著包括Gray's Anatomy,都是把膜解剖名词分散在各章中加以介绍,甚至Terminologia Anatomica收录膜解剖术语也是如此,比如盆腔的膜解剖术语就分散在括约肌系统(盆腔内筋膜,endopelvic fascia)、生殖系统(宫骶韧带,uterosacral ligament;主韧带,cardinal ligament)、腹盆腔(圆韧带,round ligament)。这就有可能导致这些解剖结构在盆腔实际是连续性的,但是在不同的部位却给予了不同的定义和不同的称谓。因此只有从膜的整体性和延续性来厘清“膜”的来龙去脉,才能统一并规范膜解剖名词。

图1-8 脏筋膜、泌尿生殖筋膜和腹下神经前筋膜是同一筋膜的不同部分
另外,膜解剖被认为是来自胚胎学的解剖学,膜解剖的科学性源于胚胎学,但实际上一些重要膜结构的演变并不清楚,肠系膜的发育目前认为经历了旋转、固定、延长和附着4个连续的过程,但我们对其具体演变机制实际知之甚少。腹膜反折作为附着这个过程的产物,Coffey[4]将其定义为位于腹后壁的壁腹膜和器官的脏腹膜之间的腹膜桥(bridge of peritoneum)。但迄今也没有关于其演变的论述,也没有发现先天性腹膜反折缺损的病例。虽然附着是在旋转阶段之后的过程,但即使在先天性肠旋转不良的病例中,腹膜反折依然存在。因此还需要进一步从胚胎学寻求和完善理论基础。
膜解剖理论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正如前述,即使解剖学上存在封闭的“系膜信封”,那么这个“信封”也是连续的,从解剖学上难以界定不同系膜之间的界限(比如乙状结肠系膜和直肠系膜),同时由于传统理论认为肿瘤的转移是无序和没有方向的,为了达到切缘的安全距离,“系膜信封”切除的范围也是人为规定的。比如德国的CME往往切除肿瘤以及远10cm的肠段及其系膜,而日本的CME的手术标本多在10cm以内[31]。因此,现行的手术在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全系膜切除或者完整系膜切除。实际上,应该从系膜的胚胎学界限来决定系膜的切除范围。Coffey[4]认为系膜与腹后壁固定的中央型机制,即系膜和血管的连接点构成了“系膜门”,“系膜门”的界限决定了清扫范围。近期的研究发现,CME的“神圣平面”即结肠系膜与Fredet筋膜(胰十二指肠前筋膜)之间平面的内侧界,位于胃结肠干和肠系膜上静脉的右侧[32]。这个对“系膜门”的新认识与近些年来日本学者对D3手术的观点转变是一致的,即沿外科干分布的淋巴结才是右半结肠癌的主淋巴结,而非传统认识上的分支动脉根部淋巴结[5]。值得注意的是,Heald[33]近期发文提出了从发生解剖学上来解释TME,这个观点认为,同一原基来源的细胞形成“腔室”,不同原基来源的细胞绝对不会跨越腔室的边界相互混合。直肠系膜构成了“直肠腔室”,“直肠腔室”内的肿瘤细胞由于遗传学上的限制而难以逾越“腔室”的边界。利用“腔室”学说可以弥补膜解剖理论的一些重要缺陷,两者的结合是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
(林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