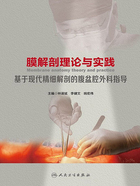
第一章 膜解剖理论概述
第一节 膜解剖的基本概念
1982年Heald提出全直肠系膜切除(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改变了传统肿瘤根治术理念,形成了“系膜信封”理论:消化道的固有筋膜包绕器官、血管和淋巴等形成了类似“信封”样的系膜,构成了肿瘤细胞难以逾越的组织屏障,局限了肿瘤细胞的转移[1]。而通过胚胎性间隙或称为“神圣平面”(holy plane),可以做到后肠“系膜信封”的完整切除(图1-1)。TME手术的出现,使得肿瘤根治术从传统的以器官为中心转变为以系膜为中心,正如Bunni[2]所言:“腹部消化道器官的肿瘤根治术不再是切除器官,而是切除器官的系膜。”这种手术理念的改变开创了新的手术方式,采取筋膜之间的间隙作为手术层次完成系膜的完整切除,如Heald的“神圣平面”、Coffey的系膜-筋膜间平面(mesofascial interface)。这种手术方式目前在临床广泛应用,在国内多称为膜解剖(membrane anatomy)[3],也有很多其他名称,如系膜解剖[4]、筋膜解剖[5]、间隙解剖(space anatomy)[6]或者层面优先(fascia space priority)[7]。

图1-1 直肠系膜与“神圣平面”
一、膜解剖概念的解剖学含义
膜解剖实际包含解剖学和手术学两层含义。人体解剖学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科学,可以分为系统解剖学(systemic anatomy,topographical anatomy)、局部解剖学(regional anatomy)和临床解剖学(clinical anatomy)。系统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分别按功能系统和人体的局部分区来研究人体结构。临床解剖学也称为应用解剖学(applied anatomy),是从临床应用角度描述人体结构的解剖学。作为一门解剖学科,膜解剖主要研究的是与外科手术相关的人体各种膜结构,如腹膜(peritoneum)、筋膜(fascia)、系膜等(mesentery),以及由这些膜结构衍生的韧带(ligament)、板(lamina)、隔(septum)、束(bundle)、间隙(space)、鞘(sheath)等各种结缔组织等相关解剖结构。与系统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不同,膜解剖研究的主要是手术操作产生的解剖结构,自然状态下并不存在,因此不能通过影像学检查(包括CT、MRI)发现。比如妇科经典解剖认为主韧带是位于膀胱旁间隙和直肠旁间隙之间的神经血管束[8],而膀胱旁间隙和直肠旁间隙都是通过手术分离疏松结缔组织产生的“空洞”样间隙,因此这些解剖结构实际都不能通过影像学检查发现,也并不在传统解剖的研究范围之内(图1-2)。从这个意义上讲,膜解剖属于临床解剖学。这种研究由手术操作产生的人工结构(artifact)的解剖学称为实践解剖学(practical anatomy),而描述自然存在人体结构的解剖称为描述解剖学(descriptive anatomy)[8]。如果说传统解剖学是“静态解剖学”,那么膜解剖就是“动态解剖学”。事实上,外科手术操作包括分离、牵拉、切开等会引起“静态”解剖结构的位置、形态发生变化。由此Yabuki[9]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Gray's Anatomy for Students这样的医用解剖学真的能指导手术吗?”

图1-2 通过建立膀胱旁间隙和直肠旁间隙产生主韧带
二、膜解剖概念的手术学含义
现在文献所论及的膜解剖更多是指膜解剖的第二层含义——基于膜解剖的手术(membrane anatomy-based surgery),简称为“膜手术”,笔者将其定义为基于特定膜间隙的完整系膜切除术。所谓的膜间隙有两层含义:一是筋膜本身即表现为间隙,多为融合筋膜(fusion fascia),如Toldt筋膜呈现蜂窝组织样特性并可作为手术平面,而在很多文献中被称为Toldt间隙[10],这与Molmenti[11]提出的筋膜间平面(interfascial plane)理论是一致的;二是指膜与膜之间存在的间隙,如Heald提出的脏、壁、筋膜之间的“神圣平面”。所谓的特定膜间隙是指能达到系膜完整切除的最内侧间隙。正如龚建平[3]所言,在广义的系膜与系膜床之间可以有4层膜和5个间隙,因此膜间隙和手术层次并不是同一概念,由于腹、盆腔筋膜存在“洋葱皮”样的解剖,因而存在多个膜间隙可以切除系膜,而只有其中一个特定的间隙才能称为手术层次,比如在直肠周围实际存在两个筋膜鞘,一个由直肠固有筋膜组成,一个由泌尿生殖筋膜(脏筋膜)和Denonvilliers筋膜组成[10](图1-3)。如果仅仅强调系膜的切除,将会忽略膜间隙与手术层次的区别,而把膜解剖简单地理解为只是“膜”之间的解剖,这会导致一种错误认识,只要进入了“微出血”或“零出血”的膜间隙就是膜解剖。日本学者Mike和Kano[5]深刻地指出了膜解剖的真谛:无所谓有几层膜,膜解剖的关键在于从不同膜构成的多个解剖层面中找寻到构成“神圣平面”的膜。

图1-3 直肠周围存在两个筋膜鞘(白虚线所示)
膜解剖如果要成为一种新的肿瘤根治术的原则,最重要的是应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1894年William Stewart Halsted首创了乳腺癌根治术,依据的理论是乳腺癌细胞首先侵犯至乳腺内邻近组织,并在血性转移发生前滞留于局部淋巴结,局部淋巴结是肿瘤细胞扩散的屏障,继而提出肿瘤根治术应做到包括肿瘤所在器官和局部淋巴结“整块切除”(en bloc)[12]。虽然Halsted的不少观点现在被证实是片面的,但其开创的现代肿瘤根治术的原则在临床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样,膜解剖如果仅仅适用于结直肠癌或胃癌,那只能称为一种新的手术方式而非新的手术理念,因此对膜解剖相关概念的定义应具有适用的普遍性。
笔者从间隙的角度来定义膜解剖,正是考虑到可以从解剖学形态和肿瘤学效应两方面来认识系膜的多样化表现,以便于膜解剖理念在临床的推广。

图1-4 “系膜门”是器官的血管、神经和淋巴管进出系膜的部位
1.从解剖学形态来讲,TME和完整结肠系膜切除术(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CME)在临床应用中取得的成功,促使学者们在其他器官中寻找具有相似解剖学形态“系膜信封”结构,但在子宫、胰腺等器官实际很难观察到封闭筋膜形成的“系膜信封”。事实上,器官的血管、神经及淋巴、脂肪、结缔组织与全身是相通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器官最外层筋膜鞘形成的封闭“信封”是相对的[13]。器官的血管、神经和淋巴管进出系膜的部位形成了系膜的“门”(hilum)(图1-4),“系膜门”的结缔组织相对疏松,并呈现为集束样包裹神经、血管和淋巴管,但没有致密的筋膜鞘[14],比如肠系膜下动脉进入直肠肠系膜的部位。器官“系膜门”的解剖形态多样,可以狭小如直肠系膜,也可以开阔如胰腺系膜。掌握“系膜门”的解剖特征可以让我们认识系膜的不同形态。胰腺系膜(mesopancreas)的概念由德国医师Gockel[15]于2007年首先提出,对其争议集中于胰腺系膜后部,胰腺与后腹膜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血管、神经、淋巴和脂肪组织,而被视为胰腺系膜,但因无明确的纤维组织鞘结构存在而受到质疑[16]。由于胰腺后筋膜与壁腹膜的融合,所以正如Agrawal[16]所言:“我们实际很难找到像直肠系膜那样围绕胰腺的筋膜。”从现有的文献报道来看,胰腺背侧系膜多描述为腹腔干和肠系膜上动脉之间,形成的一个收口状包绕,内有大量的神经、淋巴管、脂肪组织等[17],这符合“系膜门”的解剖特征。同样的,宫颈癌手术强调主韧带的清扫,事实上泌尿生殖筋膜和膀胱腹下筋膜之间即为主韧带[18],主韧带也可认为是子宫系膜的“系膜门”(图1-5)。
“系膜门”部位是疏松的间隙,并没有筋膜结构[14],这是笔者从间隙的角度来定义膜解剖的主要原因。从这个定义出发,可以辨识“系膜信封”的多种解剖学形态,从而拓展膜解剖的应用范围。现行的全胰腺系膜切除术(total mesopancreas excision)基本都是从间隙的观点来阐释膜解剖,例如胰腺实质和肠系膜上动脉之间的门静脉后层(retroportal lamina)[19],胰头和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之间的胰腺主要血管韧带(pancreas-major arteries ligament,P-A ligament)[20],实质上都是间隙。这些间隙的存在可以有两个解释,一是胰腺后方的间隙是融合筋膜的表现形式,类似于Toldt筋膜;二是胰腺后方的间隙是胰腺系膜的“系膜门”所在位置。
应重视“系膜门”的解剖概念,“系膜门”构成了完整系膜切除的界限,决定了区域淋巴结的清扫范围。理论上讲,腹腔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和肠系膜下动脉进入系膜的位置构成了“系膜门”(图1-6),这是有胚胎发育学依据的,这三根血管在胚胎期分别供应前肠、中肠和后肠(图1-7)。“系膜门”的位置决定了完整结肠系膜切除术(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CME)实际上包括了第3站淋巴结的清扫(图1-4),这与Hohenberger[21]的描述是一致的,中央结扎主要供养血管应在肠系膜上动脉的发出处。第2站淋巴结位于系膜内部,是达不到完整系膜切除的。

图1-5 子宫系膜的“系膜门”(白虚线所示)

图1-6 第5周消化道的腹、背侧系膜

图1-7 腹腔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和肠系膜下动脉进入系膜处构成了系膜门
2.从肿瘤学效应来讲,如果拘泥于既往胚胎学上演变而来的器官整体系膜,而忽略了其肿瘤学效应的本质,也是难以推广膜解剖理念的。这是因为在有些器官中,虽然存在“系膜信封”的解剖形态,但很难做到完整切除,比如胃的膜解剖。因为胃系膜形态分布极不规则,如果拘泥于传统的“系膜信封”理论,势必需要通过胰后间隙(广义Toldt间隙),将胃背侧系膜连同胰腺一并自后腹壁分离至中轴线进行完整切除,这实际并不现实也不允许[22]。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涉及对“系膜信封”肿瘤学效应的认识。由于系膜筋膜构成了肿瘤细胞难以逾越的屏障[1],“系膜信封”在本质上起着局限了肿瘤细胞的转移的作用,也就是局限了龚建平教授所说的“第五转移”[3]。因此可以把凡是由筋膜围绕而形成的、包含有神经、血管和淋巴等在内的解剖结构都认可为“系膜单位”,而传统认识上的器官系膜实际上是由多个“系膜单位”组成。近期提出的胃癌的分区域完整系膜切除[22]以及胃背侧系膜近侧段分为6个部分[23],实际就是把传统的器官“系膜”再细化为多个“系膜单位”,这里的“系膜单位”也可称为“亚系膜”,类似于Höckel发生解剖学(ontogenetic anatomy)的亚腔室(subcompartment)。同样,也存在多个“系膜单位”组成的解剖结构超出了传统器官系膜的范围,笔者称之为“元系膜”,相当于Höckel发生解剖学元腔室(metacompartment)。笔者基于“四筋膜、三间隙”理论提出的直肠癌侧方淋巴结清扫术[24],其中的“四筋膜”形成了超出传统“直肠系膜”范围的多个“元系膜”,相当于Höckel发生解剖学元腔室(metacompartment),而“三间隙”则构成了相应“元系膜”切除的“神圣平面”。因此笔者从间隙的角度定义膜解剖的原因,主要在于可以通过间隙划分不同类型的系膜,改变了仅仅通过器官的“系膜信封”这个解剖学形态来认识系膜的弊端,有利于膜解剖理念的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
(林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