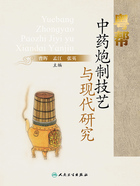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岭南中药业简史
岭南,是指我国南方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以南的地区,古为百越之地。现代岭南地区的核心位于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学界习惯把广东称“岭南”。故明清以后尤其近代和当代的岭南医药学相关研究主要面向广东省。岭南地区,气候、风土、物类等自然条件与中原不同,同时人的体质、生活习惯、疾病、生产活动等人文与经济条件亦不尽相同,以上各因素的长期组合联系造就了独特的岭南中医药学。岭南中医药学与中原中医药学一脉相承,它是中医药学在岭南独特地理气候条件和人群体质情况下,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变通与运用的产物。关于岭南中药业发展史的相关报道较少,仅有的报道也只限于中成药、厂店史[1,2]。纵观典籍,岭南中药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秦代,经历了启蒙、发展、繁荣、鼎盛和规模化精细分工的不同阶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流派,出现了一些名优中药产业及很多家喻户晓的老字号药业,故本章拟通过对岭南药材、饮片、成药、药铺(药店药厂)等中药业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剖析岭南特色中药的传承和发展。
(一)秦汉至南北朝(公元前221—公元589)
《广州府志·列传二十九》记载:“秦安期生,琅琊人,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始皇异之,赐以金璧直数千万……安期生在罗浮时尝采涧中菖蒲服之,至今故老指菖蒲涧为飞升处。”[3]可见早在秦代,罗浮山就有人采药治病。这也证实岭南地区中药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前221—前206),至少已有两千余年。1983年,在广州市象岗山发现了西汉第二代南越王(逝于公元前122年)墓,从墓中出土的文物有药物(雄黄、硫黄、紫石晶、绿松石、赭石等五色药物,羚羊角等)、捣药工具(铜臼、铜杵、铁杵等)及银盒(盛有半盒药丸)、药 饼[4]。这说明西汉时期岭南已经出现了中药丸剂等成药形式。
晋代葛洪(283—363)在广东罗浮山修道炼丹,所著《肘后备急方》记载了不少中成药剂型,如膏剂、丸剂、锭剂、条剂、炙剂、饼剂等[5]。东晋时代(317—420),有医僧在广州海福禅院(现广州海珠区海幢寺旁)问病售药,所售药品对麻疹、热疹、小儿热证发热疗效极佳,珍稀难得,故称“金汁水”,这应该是岭南成药的最早记载[6]。由上可知,岭南中药业起源于秦代,在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已有应用岭南特色药物资源行医治病的记载,除此之外,矿物药的逐步应用、制药工具的多样化、中成药的多种剂型,以及最早的岭南成药——金汁水的出现,均见证了岭南药业的启蒙时期,为岭南药业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隋唐至元(589—1368)
唐代,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对外港口,也是进口南药的主要集散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回国路经广州时,看见“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7]。五代前蜀李珣所著《海药本草》收录了从海外(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地区,直至欧洲和东非地区)输入中国的药材,如延胡索、丁香、胡椒、阿魏、沉香、龙脑(冰片)、骐 竭(血竭)、诃梨勒(诃子)、琥珀、无食子(丹宁制剂)等上百种[8]。由此可见,广州的中药贸易活动早在1 300多年前的唐代已经相当活跃。同时,唐代政府开始设置由岭南行政主管负责的海关官员“市舶使”和外来商品交易区,并初步设定理论税收政策。据《广东通志》载:“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使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来,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番人谓二百斤为一婆兰;次曰牛头舶,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舶,曰料河舶,递得三之一。贞观十七年(643),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9]可见广州港口的海外贸易在当时已颇具规模,尤其是外来胡(香)药。
竭(血竭)、诃梨勒(诃子)、琥珀、无食子(丹宁制剂)等上百种[8]。由此可见,广州的中药贸易活动早在1 300多年前的唐代已经相当活跃。同时,唐代政府开始设置由岭南行政主管负责的海关官员“市舶使”和外来商品交易区,并初步设定理论税收政策。据《广东通志》载:“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使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来,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番人谓二百斤为一婆兰;次曰牛头舶,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舶,曰料河舶,递得三之一。贞观十七年(643),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9]可见广州港口的海外贸易在当时已颇具规模,尤其是外来胡(香)药。
宋代,造船技术突飞猛进,加之政府鼓励到海外经商,故海上航路不断扩展,海外药物贸易空前繁荣。广州地区的中药商业已兴盛,其经营方式既有前店后厂的“药铺”,行医、售药、制药三位一体的“医药合营”,也有药业管理的官办机构,如惠济药局和惠民药局[6]。北宋毕仲衍所著《中书备对》记载:熙宁十年(1077),全宋有3个口岸向外商收购乳香,广州一处就购得34.87万斤,占进口总量的98%[10]。《广东通志》载:“宋开宝四年(971),置市舶司于广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淳化二年(991)始立抽解二分。凡诸番之在南海者,并通货,以金锡缗金,易其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鼍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番布、乌樠、苏木、胡椒、香药等物。太宗置榷务于京师,诏诸番货至广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9]可见北宋政府于开国之初便很重视外来商品贸易,不仅沿袭唐制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市舶司”管理外来商舶,还规定象牙、犀角(现为禁用品)、乳香、玳瑁等珍奇之物由官府垄断经营,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和税收。
从元代(1271—1368)起,广州就出现了“成方”药店,将一些颇有通行的固有成方制备以待客,如被称为药洲的成药店(现广州西湖路“药洲”遗址)[6]。同时,元代政府积极推行管药局体制,如湖广韶关府(今广东韶关市)开办惠民药局,不仅向社会供应药品,还组织药材南北交流,扩大官药局职能范围[11]。隋唐至元代的700余年,基于岭南尤其是广州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岭南中药贸易趋于活跃,由此大大促进了外来药物的发展,并形成繁荣的中外药物交流的商贸景象。政府也在该时期设立机构对中药贸易进行管理,实行税收制度,如市舶使、市舶司。同时期,药铺、医药合营的民间组织和官办机构纷纷设立,并自元代开始出现成药店,即现代药店的最初形式,标志着药业体系初步建立(并在不断完善 当中)。
(三)明代(1368—1644)
明代岭南出现医药商品生产手工业及商业,标志之一便是药铺(店)、药号的广泛兴起。有史可证的就有梁仲弘、何弘仁、陈李济和冯了性等老字号(表1-0-1),制售的剂型主要有丸、散、膏、丹、茶、油、酒等[12]。当时,佛山地区有成药作坊、厂店近百家,从业人员逾千,品种近千个,以古方正药、炮制精良、品种齐全、适应性广、疗效显著、价格低廉而负盛名。佛山因而有“岭南成药发祥地”“广东成药之乡”之称。现今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南洋、北美洲一带很多传统的成药,都源于佛山。岭南特色剂型以蜡丸名气为大,佛山商号多称之为“蜡丸 馆”[12]。蜡壳药丸具有独特的生产工艺,其中蜡壳是由蜂蜡与木蜡混合铸成的,药丸裹在其中,再用蜡密封。由于大多数中药材中含有糖、淀粉、挥发油等成分,极易吸潮、霉变或虫蛀,而用蜡壳包裹,可保留百年而不变质。清代《粤东笔记》记载:“南方草木入药者甚夥,市人制丸裹蜡,俗称广丸,远方携用颇验。”[13]其中,岭南成药“鼻祖”梁仲弘的抱龙丸可谓佼佼者,如清代《广东新语》记载“广中抱龙丸为天下所贵,以其琥珀之真也”[14]。
表1-0-1 明代岭南著名老字号药业

明代对成药的原料饮片质量和炮制技术极其重视,如陈李济广集古代固有成方、验方,秉承配方严谨,选料上乘,且奉行“工艺虽繁,必不减其工;品味虽多,必不减其物”的传统炮制宗旨。细究“选料上乘”,如应用中药阴枝的就不用阳枝,应用根茎的绝不用其茎叶。严格遵古炮制规范,如炮制鹿茸末,必须选用东北枝茸,规定火燎去绒毛,这是因为茸毛会引起咳嗽,须清除干净;生茸服后会拉肚子,须开片后再用酒炖透。经过一系列独特加工炮制才生产成药应用,使药物能发挥最佳效力[12]。
综上分析,明代的岭南中药业在规模和产品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医药商品生产手工业及商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在该时期形成的著名老字号,如梁仲弘蜡丸馆、陈李济、何弘仁、冯了性等,至今仍被津津乐道。还开发了具有独特工艺的剂型——蜡壳药丸,经受了岭南地区易霉变、易虫蛀的不良气候环境的考验。同时形成精良的饮片炮制加工技术,使老字号及其产品流传至今,带动了岭南中药业的发展与繁荣。
(四)清代(1644—1911)
清代岭南药铺、成药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广佛、港澳等地既是岭南药材的主要集散地,又是著名的成药生产基地和外贸港口,中药商贾云集,商铺林立,贸易繁荣。清初有史可证的成药就有顺德黄恒庵的乌金丸、佛山潘务本的十香止痛丸。另据《参药行碑记》记载,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仅在约200米的佛山豆豉巷中,就有27家经营药业的店铺[15]。此外,佛山畸岭街有药材会馆,并形成药材市场,发卖川、广道地药材(高良姜、广陈皮、广藿香、广巴戟、砂仁、益智、沉香、广地龙、金钱白花蛇等),贵重、大宗商品(龙涎香、燕窝、鹿茸、沉香、桂皮、大黄、姜黄等)及成药等[11]。
从康熙朝至宣统朝,广佛地区先后成立一大批民间药店、成药铺,仅有名号可考的就有近百家,出售成药数百种。部分店铺详细资料见表1-0-2。此外,还有梁昌和(1843年)、泰安药房(1882年)、春寿堂(1886年)、橘香斋药店(1895年)、善德堂、邹家园、罗广济、嘉宝栈(1902年)、广祯祥(1902年)、华天宝(1908年)、必得胜药行(1910年)、敬和堂(1911年)等[1,2,16]。当时这些药铺基本上属于前店后厂式生产成药的作坊,从药材的拣选、切铡、研磨、拌和至制成药丸、丹、散等全过程,都是靠手工操作完成,而每个小作坊都有其畅销产品。尤其以明代首创流传下来的各种蜡壳药丸声誉卓越,使这种古老剂型历经沧桑而不断发展。
表1-0-2 清代岭南主要药业

续表

注:“—”表示不详。
道光以来,广州药业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行业,逐步形成广州著名的药业八行 (表1-0-3),即“南北”“西土”“参茸”“生药(商品药材)”“生草药(民间草医)”“药片(饮片炮制)”“熟药(成药制造)”“樽头(商业零售)”等8个行业,各有不同的行头(行会)[17]。行会既是一种联络沟通行业作用的民间组织,又是征收商业税的官方代理机构。据统计,道光十三年(1833)输进广州的药材有直隶(今河北)的人参、枣子,山西的麝香,甘肃的水银、麝香,四川的麝香,云南的麝香、槟榔,两湖的大黄、麝香、槟榔、蜂蜜,河南的大黄、麝香、杏仁、蜂蜜等。广州输出的主要是进口南药(豆蔻、乳香、没药等)[18]。
表1-0-3 清代药业八行

续表

注:“—”表示无。
此外,还形成了商业行会、会馆组织(表1-0-4)。工会组织如广州药片业工会、参茸桂蔻珠射冰片工会、中药炮制配剂业工会、熟药丸散工会、南北药材工会、生药业工会等[17]。
表1-0-4 清代药业商业行会、会馆

续表

注:“—”表示不详。
香港药业铺户集中于文咸西街、永乐西街、高升街、松秀东西街一带,经营活动与广州、佛山一样有药业八行之分,药材、成药的转口贸易日益活跃[17]。《香港杂记》记载:“……余则有药材铺。”[19]《澳门记略》记载:“食货则有厚福水、药水,花露水即蔷薇水,以琉璃瓶试之,翻摇数四,泡周上下者为真;茶靡露,以注饮撰,蕃女或以沾洒人衣;药露,有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计,冰片油以瓢计。”[20]港澳地区不仅药材铺经营中药,且一般杂货店、海货店也销售各种各样的药露,如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冰片油等。清代时期岭南医药商业达到鼎盛时期,药铺、成药业发展迅猛,仅有名号可考的就有近百家药店药铺,出售成药达数百种。兼之广佛、港澳等地逐步形成的岭南药材主要集散地的优势,以及成药生产基地和外贸港口地位的确立,进一步提升了岭南中药贸易的繁荣。在这个时期还形成了广州著名的药业八行、商业行会、会馆组织、工会组织等,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岭南医药向规范化和规模化的继续发展。
(五)民国时期(1912—1949)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使广州进一步成为华南的中药材集散地,加之毗邻港澳,进口药材都经广州转运内地,于是驰名的“广药”由此得名。当时中药经营成行成市,除了熟药店、生草药店分布在全市各街道之外,各药商多集中于西荣巷、仁济路、水月宫以及仁安街、晋源街一带。此时的中药铺,也开始兼营“药食同源”的杏仁、百合、莲子、桂圆肉、蜜糖等属于京果行业的品种[14]。广州药业一片繁荣,而且出现了商品广告和企业跨省、跨国发展的现代经济形态。
据民国十九年(1930)《广州年鉴》记载,广州市有熟药(包括膏丹丸散)店铺1260间,生药铺92间,参茸店88间,药油店31间,药酒店6间,戒烟药料店42间[21]。另据民国十七年(1928)统计,佛山药业分3个自然行业,即药材103户、生药业34户、西药业9户,此外还有医业9户。代表性的药厂有太和洞药厂(1918年,靳太和)、唐人中药厂(1921年,颜英南)、陆老七药行(1921年)、灵芝堂(1921年)、邹家园药厂(1932年,邹铭德之父)、永德祥(1935年,禤新)、何济公药行(1938年,何福庆)、胜利药号(1947,李金寿)[16]。这些药厂所产药品,畅销岭南地区,行销全国各地。
另据民国二十年(1931)《中国年鉴》(China Yearbook)记载,1929年通过广州口岸输出医药约43万担(合527万余香港两),远销港澳、日、新、印、菲、荷、英、俄、德、法、美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22,23]。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底,随着京汉铁路的开通,各地不少客商来广州采购药品,刺激广州药业的迅速发展。广州全市的药材铺又发展到300多间,购销两旺,中药材的各种专业分工经营较前更具规模[23]。
民国时期,岭南中药饮片加工炮制技艺独特,有永德祥、成昌中、合和祥、裕兴祥、合兴和5家著名的药店(表1-0-5),其品牌产品均畅销广州市和四乡、海南、香港、澳门等地[24]。另外,采芝林作为当时广州著名的药铺之一,民国二十二年(1933)由黎氏第五代子孙黎子铭掌管,以经营中药饮片为主,兼营一些丸散膏丹等成药,其经营方式仍坚持前店后作坊的经营特色不变,即前店卖药、坐堂医生诊病、后场制药,集行医、制药、售药于一体,且增加了贵细药材如参茸、麝香、熊胆、珍珠、牛黄、燕窝、羚羊角、犀角(现为禁用品)等的经营,在同行中药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与地位[24]。民国时期,岭南地区中药业出现了跨省、跨国发展的现代经济形态,中药业出现专业分工,经营规模化,同时形成岭南独特的品牌中药饮片,如卷茯、手刨元胡片、火炮天雄等,远销国内外。
表1-0-5 民国主要药店

注:“*”为现在的广州市荔湾区。
(六)结语
岭南地区位于中国南端,南濒海洋,地理位置特殊,在中药贸易发展中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其中心城市广州地处珠江出海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对外港口,又毗邻港澳;另一中心城市佛山“地处三江会流处”;两大中心城市,成为华南中药材和进口南药的主要集散地,同时又是著名的成药生产基地和外贸港口。通过对广州、佛山等主要城市中药业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能粗略展示岭南地区中药业发展脉络。岭南中药业起源于秦,在秦汉至南北朝时代发展缓慢。唐代中药贸易活动相当活跃,海外贸易颇具规模。宋代海外药物贸易空前繁荣,中药商业已兴盛,经营方式既有前店后厂的“药铺”又有药业管理的官办机构。在元代出现“成方”药店。明代出现医药商品生产,药铺、药号广泛兴起,成药业作坊、厂店近百家,形成岭南特色剂型蜡壳丸。清代中药业达到鼎盛时期,药业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行业,形成广州著名的药业八行。民国年间,随着粤汉铁路、京汉铁路通车,进一步促进中药业的贸易发展,出现了商品广告和企业跨省、跨国发展的现代经济形态。
通过对岭南药业发展史的初步整理,分析了岭南药业史的发展进程和各个时期的特点,为岭南药业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岭南药业的发展过程,兼具了岭南药业产品和商贸的同步发展,形成了岭南成药的雏形(金汁水)、岭南特色剂型(蜡壳药丸)、著名的百年老店(海福禅院、陈李济、梁仲弘蜡丸馆、敬修堂)、独特的饮片炮制加工技术(手刨当归片、手切北芪片、刨制茯苓片、手刨元胡片、自创火炮天雄、手刨川芎片、手刨法半夏等)、享誉国内外的牌优产品(梁仲弘抱龙丸、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李众胜保济丸、梁财信跌打丸等)。通过对岭南药业形式及特色的梳理和凝练,以及对其特色技术、剂型和名牌产品的整理和总结,为岭南中药业的传承、技术发展和创新、学术研究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线索,为岭南中医药文化内涵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朱盛山,聂阳.传统岭南药业简介[C]//中国药学会.2006第六届中国药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广州:中国药学会,2006:2988-2993.
[2]孔祥华,刘小斌,裴芳利,等 .明清时期广东中药业历史初探[J].中医文献杂志,2010,28(6):47-49.
[3]戴肇辰,苏佩训,修.史澄,李光廷,纂.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光绪广州府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4]刘小斌,陈凯佳.岭南医学史:下[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4.
[5]葛洪.肘后备急方[M].汪剑,邹运国,罗思航,整理.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6]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工商经济史料:第二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7]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M].汪向荣,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8]李珣.海药本草:辑校本[M].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9]阮元,修.陈昌齐,刘彬华,等纂.广东通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毕仲衍.《中书备对》辑佚校注[M].马玉臣,辑校.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11]唐廷猷 .中国药业史[M]. 2版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7.
[12]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老字号:下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13]李调元.粤东笔记[M].上海:上海会文堂书局,1915(民国四年).
[14]屈大均 .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广东省佛山市博物馆.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16]佛山市医药总公司.佛山市药业志[M].佛山:佛山市医药总公司,1992.
[1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18]罗一星 .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J].广东社会科学,1987(4):82-92.
[19]陈鏸勋.香港杂记:外二种[M].莫世祥,校注.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20]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M].赵春晨,点校.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21]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广州年鉴[M].广州:奇文印务局,1930(民国十九年).
[22]奥宫正澄.中国年鉴[M].上海:上海日报社,1931(民国二十年).
[23]薛愚.中国药学史料[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24]周路山.中药世家采芝林: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发展史[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