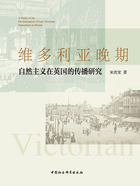
绪论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自然主义开始在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等国传播,对诸多国家的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一份世界性的文学遗产,自然主义文学理念和艺术手法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并非过时之物,认识和把握自然主义在世界诸多国家的传播及其效应意义,关乎自然主义的历史演变与价值重估,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自然主义文学的发生变迁
19世纪是欧洲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文艺大繁荣的一个时代。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的工业革命,使得欧美各国的工业取得了迅猛发展,改变了社会的物质现状和阶级秩序。由工业革命产生的重视物质利益和务实的唯物主义倾向,引起了当时社会价值标准和理想观念的变化。同时,欧洲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等科学现象的发现,将科学的探究范围从自然科学延展到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在促进社会意识发生巨变的同时,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文化思想的盛行,对传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面对社会历史、科学发展、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文学领域的变革也在悄然进行。彼时的欧洲文坛上,福楼拜解剖式的冷静观察和细致描写人物的方法、巴尔扎克注重完整性及受益于当代生物学和动物学成就的创作风格、巴那斯派(又叫“高蹈派”)宣扬艺术至上的观念方法对传统写实手法的深化等,为自然主义的出现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龚古尔兄弟合写的小说《热米妮·拉赛朵》(1865)以及具有宣言性质的序言,标志着自然主义文学的初步形成。
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左拉以革新者的姿态,积极回应社会历史变革,批判继承写实文学传统,借鉴融合实证与科学话语,跨界将文学与绘画艺术联姻,逐步确立了自然主义的文坛地位。左拉撰写的《我的仇恨》(1866)、《〈黛莱丝·拉甘〉序言》(1868)、《实验小说论》(1880)、《戏剧中的自然主义》(1881)、《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等一系列著述的发表,则逐步使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理论化和系统化。这一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形态,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范式和审美期待,为文学的言说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期,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在法国经历了从“五人聚餐会”到“龚古尔的顶楼”[1],再到“梅塘集团”的发展变迁。“梅塘集团”被认为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最为正式、最有影响的团体,主要成员有左拉、保尔·阿莱克西、亨利·塞阿尔、莱昂·埃尼克、于斯曼和莫泊桑。为了扩大自然主义的社会影响,在梅塘的一次聚会上,由莱昂·埃尼克提议,经团体成员同意共同创作一本以1870年普法战争为主题的中篇小说集(即《梅塘之夜》),并宣称坚守“源于同一理想,共信一种哲学”的文学理念。
《梅塘之夜》在出版后不到半月虽重印了八次,但它的出版也意味着“梅塘集团”分散的肇始,集团内的各个成员逐渐开始远离自然主义,当时在报刊上曾有人给“梅塘集团”起了一个外号叫“左拉的尾巴”。这归咎于“梅塘集团”成员主张的文学理念仅仅是作为一种宣传口号,而没有在创作中贯彻执行,实际支配集团成员创作的并不是某种统一的理论法则,而是各自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个性,因而与自然主义疏离是迟早之事。何况从1884年起,那些曾经信奉和支持自然主义的人员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
1887年8月18日,由班讷坦、德斯卡夫、玛格利特、居奇、罗尼斯兄弟在《费加罗报》联名发表《五人宣言》(le Manifeste des Cinq),公开反对左拉领导的自然主义,对左拉及其作品进行攻击:“左拉每天都在违背他的纲领……他越是鼓吹作品朴实无华,就越显得软弱无力,文章啰嗦冗长,一派陈词滥调,使得他最热心的弟子们不知所措……《卢贡—马卡尔家族》一书之所以吸引人,并不是其文学质量,而是由《人民之声报》吹起来的,是以描写色情而名声远扬……”[2]诚然,左拉从未苛求年轻追随者和朋友们遵从自然主义,但《五人宣言》对左拉的否定显得绝对而彻底,似乎预示了法国自然主义的命运走向。
1891年,巴黎《回声报》向文学界提出了关于自然主义的三个问题:一是自然主义病了吗?死了吗?二是自然主义能不能得救?三是代替自然主义的是什么?向文学界征集所得的答案表明,自然主义的衰亡似乎不可避免,就连左拉本人也表现出些许的不自信。1893年,左拉依然坚守着自然主义,但在完成小说《巴斯卡医生》后,开始转向空想主义小说“三福音”“四名城”的创作。莫泊桑则将主要精力放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如《蛮子大妈》《菲菲小姐》等短篇小说因描写准确和语言精辟备受读者青睐。塞阿尔则因消极情绪而离开自然主义,创作了《美好的一天》《海边出售之地》等具有伤感情调的作品。于斯曼创作了《逆流》《那里》等作品,表明自己从自然主义向宗教及神秘主义的转变。虽然说,众多的自然主义追随者满怀热情地投入保卫自然主义的战斗中,但终究各怀夙求而分道扬镳,自然主义的存在犹如飘曳的秋叶。
莫泊桑、爱德蒙·龚古尔去世之后,自然主义的衰退之势更为明显。左拉无不悲伤地向朋友诉说道:“我的心情十分忧伤,因为我过去的生活又有一部分离我而去了。渐渐地,我们的文学团体就剩下我一个人了。”[3]1897年,左拉在《致青年的信》中再次重申自然主义,但自然主义的呼应者寥寥无几,这再次印证了自然主义的衰落。尽管如此,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对真实性、科学性、客观性的强调,“实验小说”理念的提出、文学与科学相结合的观念等,不仅在法国传统文学话语中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影响到世界诸国文学的发展。
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现象,自然主义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从19世纪后期至今,学术界在自然主义理论和文学实践方面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4]国外学术界对自然主义的研究大致集中在自然主义理论、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两个方面。研究成果运用社会道德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符号学、神话学等多种方法,运用不同的视角思路和依凭不同的理论立场评价自然主义,观点迭出,各具特色。值得提及的是,1955年,左拉的儿子雅克·左拉与皮埃尔·科涅共同创办了《自然主义备忘录》(Les Cahieis Naturalists)杂志,为自然主义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随着“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出现,国外的自然主义研究借鉴法国现代、后现代理论资源与学术话语,研究范式日益与时代的精神状况呼应契合,研究维度由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转换,由文学领域的单向度研究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拓展,研究成果日趋细致入微,显现出多元视角的面相。
在国内,学术界对自然主义的研究经历了从20世纪20年代的短期提倡,到30—70年代的长时间冷落,再从八九十年代的重视与重评,以及到今天数量质量提高的阶段。若从1904年算起,自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有一百多年了,国内学术界在对待自然主义的态度上,经历了从初步肯定到批判否定,再到重新审视的阶段转向,对自然主义的理解和评价呈现出两个方面的问题域:一是在研究趋向上,评论者逐渐意识到自然主义的功过参半,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辨析、文学理念、创作方法、文本实践等问题有了微观深入的认知和阐释。二是在价值尺度上,与国外相比,国内对自然主义的整体关照大多囿于社会学批评的框架,采用现实主义的价值标准去评价自然主义的创作艺术,缺乏理论分析的深度和批评方法的更新。趋向的总体变化一方面说明社会文化语境在自然主义文学评价中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说明研究正在逐步深入自然主义的逻辑内部,但离中心尚有距离,存在的不足显而易见。故此,探寻新的批评范式、新的阐释角度、新的视角方法,无疑是国内自然主义研究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二 自然主义文学在欧美诸国
自然主义之所以具有持久广泛的影响,一方面源于在文学变革的年代,自然主义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诗学体系,谁也无法否认其存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于,自然主义在推动法国文学发展的同时,积极地参与或介入世界诸多国家文学的发展,谁也无法抹杀其影响的广泛性。自然主义在欧美诸国的命运各不相同,但其传播都无一例外地对各国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下面以德国、意大利、美国为例进行阐述。
从传播时间来看,自然主义在德国的传播和兴起要比它在法国的勃兴晚几年,其兴盛的时间是1880—1890年。在欧美国家中,德国自然主义创作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自然主义不是始端于小说领域,而是起步于诗歌领域。在诗歌领域,哈特兄弟派的威廉·阿伦特(Wilhelm Arent,1864—1921)和“突破”诗人协会的霍尔茨具有代表性。威廉·阿伦特主编的诗选《现代诗人的性格》(Moderne Dichtercharaktere,1884)被看作是德国的第一部自然主义诗集。霍尔茨出版的《时代之书:一个现代人的歌》(Das Buch der Zeit:Lieder eines Modernen,1886)则是自然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在1899年出版的《诗歌之革命》中,霍尔茨试图在诗歌领域发动一场自然主义革命,希望将自然主义诗歌发扬光大。但是,自然主义偏重叙事的特征,实际上很难在诗歌这一题材中大展身手,加上追随者寥寥,自然主义诗歌在德国的影响和成就并不大,根本原因在于自然主义的创作理念并不适合诗歌这一艺术体裁。
与法国不同,德国的自然主义戏剧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豪普特曼、霍尔茨在借鉴法国自然主义手法的基础上,运用“分秒不漏地描写”“照相录音手法”等“彻底的自然主义”手法,大量使用日常口语、方言,细致描绘人物的姿态和行动,模仿人物之间的对话,忠实刻录音响等技巧,拓展了自然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豪普特曼因剧作《日出之前》被视为德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霍尔茨和施拉夫合写的剧本《泽里克一家》(Die Familie Selicke,1890)则被看作是“彻底的自然主义”的典范。
当然,在关注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成功时,也不能忽视德国自然主义在小说领域的探索。这不仅体现在,霍尔茨和施拉夫合作的短篇小说集《哈姆雷特爸爸》、豪普特曼的《道口工蒂尔》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特色。更为重要的是,德国自然主义在小说领域出现了名为“柏林小说”(Der Berlinner Roman)的新样式。[5]就德国自然主义的创作而言,自然主义对德国产生的反响应该是最强烈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欧洲“大家公认无可置疑地存在着自然主义文学的两个国家是法国和德国”[6]。结合德国文学的历史来看,这一判断基本准确。
意大利自然主义文学兴起较早,自然主义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在意大利传播。意大利真实主义文学历来被学界看作是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最为接近的一个流派,代表作家为卡普安纳和维尔加。卡普安纳不仅提出了真实主义的诗学原则,而且对其有所实践,其长篇小说《姬雅琴塔》(1879)讲述了一个受父母冷落并被人奸污的女子的悲剧一生,呈现出左拉式的自然主义风格。《香气》(1891)则采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集中表现了人物在环境影响下所出现的生理和病理特征。维尔加阅读学习左拉作品和达尔文著作,可谓对自然主义深谙于心。由《安东尼师傅》几经修改成的长篇小说《马拉沃利亚一家》(1881)和《堂·杰苏阿多师傅》(1889)体现出“真实”“科学”以及“决定论”等自然主义特色。若要说意大利真实主义有何特点的话,那就是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意大利真实主义作家在文体上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在叙事手法上采用“民间叙事”[7],以“可与民间叙事相媲美的艺术力量”再造了事件。[8]维尔加的《格拉米亚的情人》《堂·杰苏阿多师傅》等小说基本运用民间故事讲述者的视角,采用当地民众熟悉的谚语,在展示当地民情民俗的同时凸显了民间叙事的特征。可以说,这些显示出自然主义与真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既源于作家不同的个人风格,更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文化语境的差异。
在欧美国家中,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自然主义从19世纪末在美国发生、发展、鼎盛,以致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美国文学中,并涌现出了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1870—1902)、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等诸多具有自然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家。如弗兰克·诺里斯因模仿借鉴左拉而创作小说,并自称为“小左拉”(或“少年左拉”),其长篇小说《麦克梯格》(McTeague,1899)与左拉的《小酒店》颇为类似,因而被视为“一部左拉《小酒店》的出色复本”。斯蒂芬·克莱恩虽然否认自己受到左拉的影响,但他的小说《街头女郎玛吉》(Maggie,a Girl of the Street,1893)和《红色英雄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1895)所具有的自然主义特色却被学界公认。西奥多·德莱塞虽坦言自己从未读过左拉的作品,但美国评论界却常将他尊奉为“美国的左拉”。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1903)、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的《屠场》(The Jungle,1906)、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等作品被学界视为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时审视,美国作家借鉴自然主义创作手法所做的实验性尝试,在革新创作题材和文学观念的同时,实际上是对“真实美国的发现”和美国文学的新探索。动态观之,这种新探索,一方面表明美国自然主义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是和人与社会的时代呼应相联系,其重心不在于生理的病态剖析,而在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辨析;一方面表明自然主义对美国的影响并不局限于19世纪末期,更重要的在于对整个20世纪美国文学的影响。
三 研究现状述评与框架设计
综观现有研究,世界各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研究状况很不平衡,成果主要集中在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美国自然主义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以及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领域,而对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零散的阶段,对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亦不例外。
(一)现状述评
在国外,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的后期(19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初)就出现了欧内斯特·维泽特勒(Ernest Vizetelly)的《左拉在英国》(With Zola in England,1899)、《小说家兼改革家左拉》(Emile Zola,novelist and reformer,1904)等向英国介绍左拉及其作品的著述。20世纪20—50年代,出现了诸如狄克(Clarence R.Decker)的《左拉在英国的文学声誉》(Zola's literary reputation in England,1928)、费里尔生(William Frierson)的《1885—1895年英国对小说现实主义的争论》(The English controversy over Realism in fiction 1885—1895,1928)等论述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及其论争的论文,但在内容上浅尝辄止。如狄克的《左拉在英国的文学声誉》一文,从作家所处的时代入手,着重描述了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取代巴尔扎克成为维多利亚社会“冒险者”的过程,认为“左拉在英国的文学声誉,表明了处于维多利亚中期时代的人在审美道德方面的性情品位”[9]。文章采用比较的方法,论述了法国文学在那一时期的演变,比较了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在英国接受的差异,但在整体上缺乏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勾勒,没有揭示出文学传播背后的文化动因。
20世纪60—80年代,英国学者弗斯特等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1978)、J.亨金(Leo J.Henkin)的《英国小说中的达尔文主义(1860—1910)》(Darwinism in the English novel 1860—1910,1963)、J.A.V.甫尔(John A.V.Chapple)的《记实和想象文学(1880—1920)》(Documentary and Imaginative Literature 1880—1920,1970)等著作对英国自然主义都有所提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英国学者琳·皮科特(Lyn Pykett)的论文《再现现实:英国关于自然主义的论争(1884—1900)》(Representing the Real:The English Debate About Naturalism 1884—1900)、比尔德(Alma W.Byrd)的专著《左拉小说在英国和美国的第一代接受史》(The First Generation Reception of the Novels of Emile Zola in Britain and America,2006)、法国学者莫尼克·热古(Monique Jegou)的论文《英国对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的接受》(La Réception des écrivains naturalistes en Angleterre,2006)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但论述都较为简略。如热古的《英国对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的接受》一文,以时间为顺序,采用比较的方法,重点分析了福楼拜、莫泊桑、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在法国的历史处境和在英国的引介反应。文章通过对自然主义在英法两国接受情况的比较,认识到了政治语境和文化背景对文学接受的影响,肯定了自然主义对英国传统小说美学的创新作用,但对自然主义在英法两国接受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缺乏明晰的论证。
在国内,关于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岳添的专著《左拉学术史研究》、高建为的专著《自然主义诗学及其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影响》及论文《从自然主义在英国的读者反应看文化适应问题》等简要梳理了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吴岳添在《左拉学术史研究》一书中以学术史的方式,比较清晰地勾勒了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情况,整体上对英国自然主义做出了客观中肯的评价。吴岳添认为,与德国相比,英国没有形成自然主义运动或团体的原因在于,英国现实主义文学悠久的历史传统,使“英国虽然有一些自然主义作家,也始终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传统”[10]。高建为在专著《自然主义诗学及其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将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分为三个阶段,分期追踪了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过程。[11]高建为的论文《从自然主义在英国的读者反应看文化适应问题》运用读者反应理论,分析了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受阻的原因。[12]刘文荣在专著《19世纪英国小说史》、张介明在专著《边缘视野中的欧美文学》中,都对自然主义在英国遭到抵制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如张介明从自然主义与各国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入手,认为英国出现的自然主义文学在创作上“追求的是正宗的‘法国式’的自然主义,而无意于改造和变化。”[13]这一观点认识到了英法自然主义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但对英国自然主义刻板模仿法国自然主义的看法并不符合文学史实。李维屏在《英国小说艺术史》中将自然主义和宿命论作为19世纪英国小说发展中的第三种倾向,[14]而王守仁、方杰主编的《英国文学简史》则认为英国的自然主义作家寥寥,和者可数。[15]
通过梳理可见,学术界对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整体论述不多,介绍性的泛泛而谈居多,缺乏细致的深入研究和系统的认知评价,并且常常将传播与影响割裂开来。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对英国自然主义的文学成就、理论建树、形态地位等方面认识不足。
客观地说,从19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20世纪初,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对英国及其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且受其影响还出现了几个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遗憾的是,受到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自然主义在英国存在的诸多史实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弱化,研究自然浮泛偏狭,至今国内未出现一部系统全面的研究专著。因此,对自然主义在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传播进行研究实有必要,深化其研究意味着这一领域具有广阔的学术增长空间。这一学术尝试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外来文学与本土文学及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促进文学文化的交流融合、凸显本民族的特色,特别对我国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框架设计
依据选题,本书主要以“自然主义”为中心,聚焦于“传播”。因而,本书在研究内容对象的设定、思路方法的设计、研究目标的实现皆围绕“自然主义”“传播”两个关键词及其相互关系展开。
1.研究对象内容
第一,探析自然主义的“世界性”。自然主义为何具有“世界性”?这是研究“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的前提基础。以“世界性”为切入点,围绕自然主义的内在“世界性”(如何生成)与外在“世界性”(如何传播)两个层面,探析自然主义生成的哲学、文学、文化、科学等共时性因素,阐释自然主义在域外的传播接受、影响建构、借鉴创新等表现形态,论述自然主义共同体的“世界性”建构,进而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文学生态等方面探究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发生的可能性契机。
第二,探讨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自然主义作品在英国的译介状况以及接受反应是本书着重研究的问题。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遗产至今依旧在英国继续传播和接受,并且比维多利亚晚期的传播更为多元,接受更为广泛,但自然主义在维多利亚晚期进入英国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最能反映英国对待自然主义的历史态度和价值立场,因而本书所论述的“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关注和聚焦于维多利亚晚期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具体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按照传播进程和接受反应,细致梳理与自然主义有关的作家如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龚古尔兄弟、莫泊桑、都德、易卜生在英国译介批评的历史脉络,比较上述作家及其作品在英国译介接受的差别,总结不同阶段传播的途径方式、媒介桥梁、文化语境等方面的特征。
二是围绕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者与翻译需求、批评论争与文学场较量、传播媒介与文学审查、传播受众与审美接受四个方面,探究出版者、批评家、创作者与大众读者对待自然主义的立场动机、文化语境和审美心理之间的连锁反应,深入阐析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互动的形态机制。
三是以英国道德话语、维泽特勒的审判、《有害的文学》等为切入点,探究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受阻的深层缘由,分析英国批评自然主义的主导话语与自然主义的价值悖论,揭示英国接受自然主义的态度反应与维多利亚时代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探析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中出现的文化过滤与冲突现象,阐发跨文化语境下英国本土经验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
四是围绕批评观念、文学类型、审美趣味和形态范式四个方面,阐析自然主义对英国文学产生的整体效应与历史意义。
第三,阐析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影响的历史演进。自然主义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主义作家提倡的自然真实、客观书写等创作观念和艺术手法,都可以在意识流等英国现代主义流派中发现或隐或现的痕迹。这一部分的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辨析英国现实主义中是否存在自然主义因子,考察自然主义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型构,重新审视英国文学与自然主义的双边关系;二是探究自然主义与意识流之间的隐性影响和逻辑衍生。
2.思路方法
对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展开研究,就需结合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的社会历史和文艺思潮发展趋势,考察自然主义与英国当时各种艺术流派、思想文化的关系,阐析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接受、发展融合的历程。
本书拟在对第一手资料和现有成果爬梳、剖析与借鉴的基础上,以“找准研究视点、突出问题意识”为导向,秉着“立足文献资料,拓展研究视域”的研究理念,坚持“论从史出、以史证论”的原则,在对“自然主义”及其“世界性”等问题界定阐发的基础上,遵循“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自然主义在英国如何传播),聚焦两个基本研究点(批评论争和互动机制)、沿着三条研究路径(宏观勾勒到微观探究、纵向考察到横向比较和个案分析到诗学建构),形成一个研究体系”的设计思路。在引入、挖掘新材料的基础上,采用逐层深入的论证结构,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拓展对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研究的深度,深化对文学传播规律的认识。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书总体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尝试运用发生学、传播学、接受美学、文化研究等方法,将动态的历史述评与静态的个案研究相结合,系统全面地对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的历程经脉、形态特征、阻遏缘由、效应意义、历史演进进行多维考察和深入探究,以建构起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的立体景象。
[1] 1874—1880年间,由福楼拜主持,左拉、爱德蒙·龚古尔、都德以及屠格涅夫五人常常于星期天共进晚餐,讨论文艺问题,探索文学创作,史称“五人聚餐会”。1885年开始,聚餐改由爱德蒙·龚古尔主持,继续在星期天举行例会,畅谈各自对文学的看法,由于地点在龚古尔家房间的顶楼,史称“龚古尔的顶楼”。
[2] [法] 亨利·特罗亚:《正义作家左拉》,胡尧步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
[3] [法] 马克·贝尔纳:《左拉》,郭太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4] 参见吴岳添《左拉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274页。
[5] “柏林小说” 是以“柏林”为书写中心,描绘其风俗民情和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小说。“柏林小说”的代表人物是被誉为“德国左拉”的马克斯·克莱策(Max Kretzer,1854—1941),其作品有《被欺骗的人》(1881)、《穷途潦倒的人》(1883)、《廷佩师傅》(1888)等。
[6] [法] 伊夫·谢弗雷尔:《自然主义诗学》,载让·贝西埃等著《诗学史》(下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607页。
[7] 与一般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不同,这种在意大利被称为“Bozzetto”“Schizzo”或“Maechietto”的文体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特写”“速写”。与左拉善于大量使用“自由间接话语”的小说叙事方法不同,维尔加主要采用“民间叙事”(popular narration)的艺术手法,实际上与左拉的“非个人化”叙事有异曲同工之效。
[8] Giovanni Cecchett,“Introduction”,In Giovanni Verga,The House by the Medlar Tree (IMalavogl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14.
[9] Clarence R.Decker,“Zola's literary reputation in England”,PMLA,Vol.49,No.4,Dec 1934,p.1140.
[10] 吴岳添:《左拉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页。
[11] 参见高建为《自然主义诗学及其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影响》,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233页。
[12] 参见高建为《从自然主义在英国的读者反应看文化适应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3] 张介明:《边缘视野中的欧美文学》,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14] 李维屏:《英国小说艺术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15] 王守成、方杰主编:《英国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