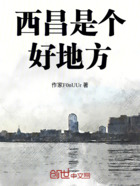
第1章 高原瑰宝—凉山西昌
抵达西昌的那日,阳光像一匹金色的绸缎,从湛蓝的天幕倾泻而下,将整座城温柔裹挟。这座被称作“小春城”的西南边陲之地,仿佛被太阳偏爱,四季的光影在此流转成一首未竟的长诗。街道旁,小叶榕的绿荫如伞盖般遮蔽燥热,彝族老阿妈背着竹篓缓步而行,银饰在阳光下闪烁,叮咚声与市井喧嚣交织成独特的韵律。
我循着风中的烟火气,走入腊月末尾的年俗里。西昌的春节,是一场从冬至便开始酝酿的盛大叙事。家家户户屋檐下悬挂的腊肉泛着琥珀色的油光,杀年猪的吆喝声在村落间此起彼伏。老茶馆里,几位“老西昌”围炉而坐,茶碗中升腾的热气氤氲着往事:“年三十敬天地,初一游百病,初二上坟山……”他们的讲述里,时光倒流至旧日:孩童们争抢压岁钱的嬉闹,龙灯队伍穿街过巷时震天的锣鼓,以及深夜绽放的烟花,将夜空染成琉璃色。
晨雾未散时,我独往邛海。这座高原湖泊静卧于泸山脚下,像一块被岁月打磨的翡翠。无风时,湖水是一面倒悬的镜子,将远山的轮廓、云絮的游移悉数收纳。偶有白鹭掠过水面,翅尖轻点,涟漪便一圈圈荡开,宛若仙人以指腹叩问大地的私语。当地人说,马可波罗曾在此驻足,惊叹“天影落虚净,山光随动摇”——千年后,我立于湖畔,仍能触摸到那份亘古的悸动。午后,风起。浪花推搡着涌向岸边,不似海潮的暴烈,却似彝家姑娘裙摆的摇曳,轻柔中藏着韧劲。渔人驾舟破浪,竹篙一点,身影便融入水天相接的苍茫。忽见一群孩童赤脚奔来,将折好的纸船放入浅滩。船随波逐流,载着稚嫩的愿望漂向湖心,恍惚间竟与古诗中“孤舟几度横”的意境重叠。
火把节的夜晚,西昌化身为光的海洋。彝族汉子们高举火把,火光如游龙穿梭于街巷,将夜色撕开炽热的裂口。广场中央,篝火冲天而起,身着彩绣长裙的姑娘们围火踏歌,银饰与火焰共舞,投下的影子在地上织成流动的图腾。一位醉酒的少年不慎让火舌舔舐了发梢,却大笑着高喊:“这是山神赐的祝福!”人群哄笑,笑声融进噼啪燃烧的松枝,升腾至星空。穿行于夜市,坨坨肉的香气霸道地钻进鼻腔。大块的猪肉盛在木盘中,彝家阿妈递来竹刀:“莫用筷子,用手撕才痛快!”我学着她的样子撕咬,油脂混着辣椒的辛香在舌尖炸开,粗犷的滋味里竟品出一丝山野的慈悲。邻桌的醉虾在酒碗中弹跳,外地游客惊得连连后退,却被老板一句“虾醉了,人才醒”逗得释然——西昌的幽默,总带着三分土地的浑厚。
城郊的彝寨隐于云雾深处。吊脚楼依山而建,檐角悬挂的牛骨风铃随风作响,恍若远古的呓语。火塘边,毕摩(彝族祭司)吟诵着《勒俄特依》,苍老的嗓音里流淌着支格阿鲁射日的传说。孩童托腮追问:“为何不射星星?”老人眯眼笑答:“留些光亮,给走夜路的人。”火光跃动,将他们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仿佛一部永不谢幕的皮影戏。
归途遇雨。山雨来得急,却在落地前被阳光截住,化作漫天金丝。彩虹从邛海尽头升起,跨越整座城池,如同神灵以苍穹为弓,为西昌系上斑斓的绶带。离别的清晨,我登上泸山观海亭。晨光中的西昌尚未完全苏醒,邛海的雾气如轻纱浮动,隐约可见早渔的舟楫。山寺钟声荡开,惊起群鸟,翅羽搅碎的光斑落进茶园——采茶女的头巾在绿浪间起伏,恍若大地绣出的碎花。
忽然懂得,为何此地被唤作“春天栖息的城市”。它的美不止于四时不谢之花,更在于那糅合了汉彝风骨的烟火人间:既有围炉夜话的温情,亦有火把燎原的豪迈;既容得下邛海千年的静默,也纳得了市集鼎沸的喧嚷。当火箭从卫星发射基地腾空而起,古老的土地与浩瀚星穹对话时,我仿佛看见,这座月城正以大地为笺,将所有的传说、欢笑与守望,写成寄往宇宙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