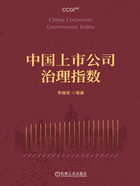
一、内部治理研究
(一)股东治理
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存在着种种关联,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行为往往超越了上市公司法人边界。中国转轨时期经济的复杂性决定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行为的复杂性,控股股东目标选择不再局限于对上市公司控制收益与成本的比较,而是更多地考虑集团整体利益。股东治理研究涉及股权结构与股东平等待遇、控股股东行为负外部性形成及制约机制、控制权配置等方面。
股权结构研究方面,早期研究多为直接探讨股权结构对公司单一结果性指标(绩效、业绩、价值等)的影响(Djankov和Murrell,2002;Megginson和Netter,2001;陈德萍和陈永圣,2011;顾露露、岑怡、郭三和张凯歌,2015;郭冰和刘坤,2022;郑志刚、朱光顺、李倩和黄继承,2021;祝继高、苏嘉莉和黄薇,2020)。还有学者从公司行为层面探讨股权结构的影响,发现低成本和稳定的投融资行为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善。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比普通股股东有更强的决策能力和判断力,且管理层掌握企业控制权,能避免其他外部股东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错误决策,因此,管理层不会去选择那些利润不高但效果显著的项目(DeAngelo和DeAngelo,1985)。优化股权结构能够满足异质化股东的多样化需求,促使公司致力于长期发展目标,有效避免敌意收购,保持公司业务稳定,进而提高其投融资的决策效率(郭雳和彭雨晨,2019)。已有研究还从管理层挪用资金等方面提出股权结构对企业投融资存在影响。同股不同权的公司管理层更有可能将其公开发行的收益进行挪用,而非用于新的投资为公司创造价值,具体可能用来收购公司或偿还债务(Arugaslan、Cook和Kieschnick,2010),因此双重股权结构下管理层可能并不重视企业的投资效率(Howell,2017;刘翔宇、邝诗慧、黄钰婷和梁嘉静,2020)。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我国公司治理改革实践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关注代理行为,实证研究了股权集中和股权职能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李寿喜,2007;尤华和李恩娟,2014)。例如,Shleifer和Vishny(1989)认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存在一致性,控股股东有动机积极收集信息并有效监督管理层,也有能力控制经营管理层,避免股权高度分散情况下的分散股东“搭便车”问题,在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Demsetz和Lehn(1985)与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1998)则指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存在利益不一致性,甚至利益冲突严重,大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追求自身利益,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侵占小股东的利益。董志强(2010)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解释了公司治理模式选择行为、现象,认为公司治理模式是基于股权结构和投资者法律保护而做出的一种适应性反应,股权较集中的国家更适合采用双层制的公司治理模式。万丛颖和张楠楠(201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股权结构具有调节大股东治理和掏空效应的作用。在调节大股东治理效应时,国有股股东的调节作用高于非国有股股东;而在调节大股东掏空效应时,国有股股东的调节作用低于非国有股股东。尤华和李恩娟(2014)以201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既可以降低股东与经营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即第一类代理成本),又可以降低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即第二类代理成本),而股权制衡度可以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但却提高了第一类代理成本。李寿喜(2007)通过考察政府管制较少、竞争比较充分的电子电器行业后得出结论,代理成本最高的为国有产权企业,其次为混合产权企业,个人产权企业的代理成本最低,说明产权改革和产权多元化能够改善公司治理。石大林、刘旭和路文静(2014)运用动态面板的系统GMM(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之间的确存在动态内生关系,前期股权集中度与当期代理成本负相关,前期代理成本对当期股权结构具有反馈效应,当期股权集中度与当期代理成本负相关,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存在跨期内生关系。
大股东和控股股东的研究方面,学者们先后探讨了大股东或控股股东控制对公司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王斌、蔡安辉和冯洋(2013)认为控股股东参与股权质押可以缓解股东的融资约束,且当该融资额投入公司发展时,表明其对公司发展充满信心,且有利于充分发挥资源的杠杆作用,改善公司绩效。谢德仁、郑登津和崔宸瑜(2016)实证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表现为负相关关系,且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风险更低。另外,高比例质押的控股股东,其丧失公司控制权的机会成本加大,控股股东提升公司绩效的积极性和市值管理需求更为强烈,公司股价崩盘的风险更小,可能更受市场支持。更多的研究表明,当法治不健全、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缺乏监督和制约时,在控制权私有收益的驱使下,控股股东会产生转移上市公司资源的“掏空”行为,从而侵占小股东的利益(Holderness,2003;Vanzo、Acquaviva和Di Criscienzo,2011)。Shleifer和Vishny(2003)认为,控制权收益仅由控制性股东独享,并非按股权比例在所有股东中分配。Claessens、Djankov、Fan和Lang(2002)指出,在世界大多数企业中,股权集中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而非管理者对外部所有者利益的侵占,控股股东通过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进行资源性的投资扩张,取得了大量超过现金流价值的控制性资产,这些资产成为控股股东控制权收益的重要来源。袁淳、刘思淼和高雨(2010)对关联交易和现金股利两种利益输送方式的收益与成本进行分析,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对关联交易和现金股利两种利益输送方式的选择也不同,即在既定利益输送程度的限制下,两种利益输送方式存在替代关系。武晓玲和翟明磊(2013)通过分析600余家上市公司的统计数据,发现具有利益输送动机的大股东,往往派发现金股利从而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机构投资者的研究方面,一部分学者关注了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意义和价值。有学者认为机构投资者是对董事会独立性不足的补充,能够对公司管理层施加影响(Boyd和Smith,1996;Parrino、Sias和Starks,2003)。董事会是缓解股东和公司管理层之间矛盾的主要力量,但如果董事会没有足够的独立性去监督和制约管理层的行为,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董事会力量的不足。并且,机构投资者有动力和能力监督公司。Shleifer和Vishny(1989)认为,为了避免因信息不对称等造成的被动损失,机构投资者将通过其获得的相对比较集中的投票权来实现其监督并提高公司业绩的动机,并在适当的时候通过纠正和实施影响以获得相应的切身收益。他们认为相对于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由于拥有资金、信息和专业优势,有能力采取股东积极主义参与公司治理,有实力去监督公司管理者。但也有学者从自身内部约束的角度,认为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取决于其投资经理的动机,而投资经理可能会因定期业绩等与自身薪酬挂钩的短期考核指标而导致相应的行为短期化,重点关注当期利润而并不关心被投资公司的长期经营和治理决策(Graves和Waddock,1990)。此外,机构投资者内部“搭便车”的行为也可能使其难以发挥公司治理作用(Webb、Beck和McKinnon,2003)。在公司行为和特征方面,唐松莲、林圣越和高亮亮(2015)发现:基金持股比非基金持股能更大程度地克服资金匮乏产生的投资不足问题;长线型基金比短线型基金更能够克服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也有部分学者得出结论,投资机构对企业的影响呈现负面作用或不确定作用。Bushee(1998)得出结论,专业机构者的频繁交易加剧企业追求短期利益性质的研发投资。此外,该研究创造性地指出了九个特征变量,以投资机构的历史行为偏好为划分依据,认为机构投资者包括准指数型、短暂型和勤勉型三种类型。Dennis和Strickland(2002)发现,投资机构参股比例变动会加重企业经营绩效的波动性。在股票市场不稳定时,投资机构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会维护企业的短期绩效,可能采取追涨杀跌的正反馈的交易机制,释放信号,进而引导市场走向更不稳定的状态,最终不利于企业的经营业绩。张敏和姜付秀(2010)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研究结果表明,适配的治理环境才能保障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在民营企业内更显著,它能明显增加薪酬对业绩的敏感性,减少薪酬黏性;相反,上述治理效应并没有显现在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中。Edelen、Ince和Kadlec(2016)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那些长期业绩相对更差的企业,有强烈的倾向去购买被分类为高估的股票,在这之后其持股行为通常会造成股价的波动。但是,机构投资者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随着治理改革的发展,学者也关注了中国情境下的治理问题。例如,在股东性质的研究方面,学者们首先关注了国有股的影响(胡芳肖和王育宝,2004),也有学者探讨了不同股权性质对公司特定行为的影响差异(袁振超、岳衡和谈文峰,2014)。还有学者关注了涉及股东治理的重大政策变动的影响,在股权分置改革方面,有学者关注了利益分配(赵俊强、廖士光和李湛,2006)、对价确定和对治理有效性的影响(郑志刚、孙艳梅、谭松涛和姜德增,2007)、改革中的锚定效应(许年行和吴世农,2007)以及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支晓强、胡聪慧、童盼和马俊杰,2014)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