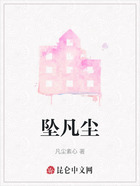
第6章 坠凡尘
爸妈执教的学校是一所高中,他俩教的科目都是英语。这在当时可是紧缺教师,尤其是在云城这样的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
其实爸爸妈妈原本也是出生在大城市的,一个是东边繁华地,一个是紧挨着那儿的江市,并且他们俩都是大学生,在那样的年代,能上大学可不容易,他俩都双双考上同一所江市的重点大学,都进了外语系。他们这样的学生,如果能顺利毕业,那都是去外事单位的,前途无量,怎么能到云城这样的地方,做了一个教书匠呢?
命运总喜欢和人开玩笑,在他们刚刚踏入那个重点大学两年的时候,一场影响了几代人的“革命”开始了……鸿儿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因为这场“革命”实在影响太深远,时至今日,还有很多关于它的文字记载或各种各样的故事,而她的身边人也有很多被影响了,她也是被间接影响了的。她后来知道,她父亲,那个还在她襁褓里时,常常抱着她的父亲也是因为这场“革命”离开了家乡,还有她和祖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总驮着她去公园玩的小舅舅,也曾去了离家万里之遥的“苦寒”之地。那时候,每家每户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不管男女,都得有人响应号召,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原籍,去一个遥远的,落后的地方去“磨练意志”,去体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那时候,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真正能体会个中滋味。
鸿儿的爸妈,在考上大学以后,竟然也要被强迫着中断了学业,去参与到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去。所幸的是,他们没被“发配”到“宁古塔”那样的地方,而是去了一个江南名城所辖地区的农场。这里离家不算远,他们心满意足了。他们在日日的农业劳作中,“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活捡累的干,事挑难的上。爸爸用扁担担起自己身体几倍重的泥土,运来运去,到了晚上,肩膀又红又肿,但睡一觉起来继续干!妈妈为了赶工,生理期仍然下到水稻田里,不顾身体不适,也要完成任务。冰冷的水,让她落下了终身的病根--关节炎。这和如今在监狱里的服刑人员待遇有啥区别?!如今的服刑人员还能享受人道!
他们就这样勤恳努力的“改造”,也在这个过程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到了要分配去向的时候,他俩不想分开,要求分配到同一个地方去。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都没被留在那个江南名城,而是爸爸被分到了云城的灵镇,妈妈被分到了比灵镇还要偏远的梅镇,但他们觉得云城离江南名城不远,离家应该也不算远,而灵镇和妈妈所在的梅镇离灵镇也不算远,他们觉得挺好。而且他们将来的工作是当老师,教书育人乃千秋伟业,他们欣然接受。可是,他们被迫中断的高校学业呢?时间都被浪费在了“改造”上,那时候和他们相同经历的人比比皆是,于是他们背上行囊便奔赴人生下一个站点……
云城是云城,灵镇是灵镇,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要呆一辈子的地方居然是农村?那个小镇,被群山环绕,大巴要开好几个小时。学校旁边都是稻田,稻田中间有化粪池,冲脑门的味道扑鼻而来,还真是原生态。农民每天早晨就从那里面舀些肥料去浇灌田地,这才是真正的有机肥!春天的时候,农民挥舞着手里的细树枝条,赶着背上套着犁架的老黄牛,吭哧吭哧地耕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真是很形象。再看妈妈那边,更偏更远,学校晚上经常停电,每个老师房间里都有一盏应急用的“美孚灯”。那就是鸿儿后来学了化学以后,拿来做实验的酒精灯,再配上一个保护火苗的长长的玻璃灯管。只不过,大肚子玻璃瓶里装的不是酒精,而是煤油。那为什么叫它“美孚灯”呢?因为这是美孚公司—一家美国公司,从事石油和石化业务,在19世纪20年代,也就是民国时期,进入中国。他们既卖灯,又卖油,是不是很聪明?但因为它方便好用,一直到70/80年代还有人在使用。这不,妈妈就用上了。那灯光在雨夜晃啊晃,照着外面树的影子也晃啊晃,妈妈一个人在单身宿舍害怕极了,只能抱紧了被子,把头蒙在被子里不敢探头。第二天,风雨停了,妈妈抱着教科书去上课,因为她长得不高,在黑板上写字,有时候还得踮起脚来,乡野长大的孩子没规矩,在后面吃吃地笑她,还不好好听课。但她刚去,年轻,没经验,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课后躲在屋里偷偷哭。她想家,想爸爸。那时候乡村里没有电话,没法让她向爸爸诉苦,爸爸只有周末的时候,骑上几小时的车去看她,给她做点好吃的。学校里的老教师注意到妈妈,便在一次爸爸去看她的时候建议到:“你们申请结婚吧,她一个姑娘家,又是城里来的,一个人确实不容易,结了婚,你们可以打报告申请到一个地方工作,我可以帮忙来协调一下。”在这位老教师的帮助下,爸爸妈妈结婚了,不久,妈妈也被安排到了灵镇的学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