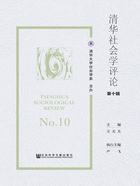
西方理论与本土化前沿
以国际化视野做中国研究:社会学研究的祛魅与回归
曹立群 杜少臣[1]
摘要:“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议题,而是一个掺杂各种立场和误解的复杂的综合性议题。社会学的发展不应停留在概念、理论是否引进的外围的学术争吵上,而是要在实实在在的社会学研究中,回到经典社会学研究所树立的品格,在对现实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中,不断发掘和反复咀嚼内在于社会学本身的价值和追求。如果本土化一定要成为一个议题,我们认为,社会学本土化的本质应该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祛除狭隘、偏执的民族主义和肤浅、短视的功利主义,祛除预设各种立场的主义,祛除所有不符合现代精神的依恋和后现代的迷思。我们主张以开放的心态、科学的态度、无问西东的精神,将中国社会学研究纳入国际视野,将社会学研究拉回学科本身的内在规律性和诉求,进而回到学术无国界的国际化轨道上来。
关键词:本土化 国际研究 情境知识 现代化“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是一个掺杂各种立场和误解的复杂的综合性议题。担心中国社会学不够本土化的思维从根源上看,很大程度上来自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大政府”及其追随者,而不是学术界。这种担心,在学术界有人响应,而响应的学者要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不甚了解,要么有其他目的。比如,担心量化研究的壮大,担心质化研究的衰微。本文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中国社会学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提高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国际地位。
一 问题的提出
社会学本土化的提出始于社会学的刚刚传入,而最近开始的相关争论则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的事。社会学在中国的发轫之初,学界前辈在大量引入社会学经典巨著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注重实地调查并积累大量数据;注重本土实证和历史经验材料的分析与引证;引入并提出新的学说;重视社会学作为实学的发展方向,参与社会行政与社会建设,并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孙本文,2011)。
早期的社会学家并没有对“社会学本土化”这一概念进行太多的讨论。吴文藻最早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在其对中国社会实实在在的研究之中提出的。他担忧“促进中国欧美化和现代化,其结果是使我们与本国的传统精神愈离愈远。事实上我们对于固有的文化,已缺乏正当认识,我们的意识中,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吴文藻,2010:438)。其目的之一在于要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极端倾向,如“砸烂孔家店”的提法在历史文化纵深和世界文化图景之中寻求坐标,并在既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知识宝库里寻找更适合做中国社会研究的一套理论和方法体系。作为其得意门生的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仍然是“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费孝通,1997)。
二人同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在对待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态度上,一方面体现了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坚定信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中国社会情境特殊性的观照。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二者都沿用社会学经典的研究范式,在中西文化社会的比较当中,以期提出与西方传统社会学研究并行的中国概念。
港台社会学家虽然更加强调科学方法的条件性和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理解脉络与取向上的不同,也有试图跳出社会学科学属性的“桎梏”来创建一门所谓的“中国的社会学”的呼吁(叶启政,2006),但是作为在学缘上与西方更为亲近,较早、较系统地接受西方社会学科学训练的一支科研队伍,其呼吁持续数十年却并未在范式上有任何实质性的超越。在实证方面,杨国枢(2004)脚踏实地,发展出更符合国人心理的量具,促进了世界对国人的了解。
作为在海外接受社会学训练的海外学派,谢宇(2018)秉持科学的立场,通过对本土化和实践中三个主要方向(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的批判性回顾)的讨论得出,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他指出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在科学的意义上为社会学学术积累做出贡献,才能真正体现社会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无独有偶,边燕杰(2017)提出本土社会学知识的国际概念化,同样强调地方性知识对学术共同体的贡献。
一方面我们不能背离基于科学方法的学科传统,另一方面更不能漠视文化展开的丰富的人性。社会学知识的获取和研究对象的确立从来都是以某一文化和某一特定时空的社会形态为起点和依据的,但是社会学知识的形成与传播却不应预设任何文化的立场,这是由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不应演化成和蜕化为不同流派和思想传统自说自话盲人摸象似的毫无意义的辩争,更不应成为偏安于一隅,在各自的文化场域中只满足于为一部分人所理解和认同的自娱自乐的本土化。社会学本土化的提出以对社会学知识普适性的认同为前提,其结果当然要以回报性的知识积累为目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如果本土化是一个有意义的议题,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就不应停留在概念或理论是否引进的外围学术争吵上,而是要在实实在在的社会学研究中,回到经典社会学研究所树立的品格,在对中国现实的不断反思和批判中,不断发掘和反复咀嚼内在于社会学本身的价值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本土化本质上应该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祛除狭隘、偏执的民族主义和肤浅、短视的功利主义,祛除预设各种立场的主义,祛除对所有不符合现代精神的依恋和后现代的迷思。我们主张,社会学研究以开放的心态和科学精神,将“社会学中国化”的议题拉回学科本身的内在规律性和诉求,进而回到学术无国界的国际化轨道上来。
社会学研究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而现代化是一个未竟的事业(Habermas,1987)。它如同变动不居的流水,尽管形态各异、流速不定,有时甚至方向莫测,但它是一个整体的、全方位的东西(Giddens,1990),千万不要把变化都当作进步。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偏重物质的现代化而忽视文化、制度的现代化,重视富国强兵而忽视以人为本。在制度与科技不匹配的路上,中国和南非一样创造出经济奇迹(秦晖,2008),社会分层与犯罪率同步增长(Cao and Dai,2001),让“官二代”先富起来(边燕杰、芦强,2014),让体制内的国企先富起来(谢宇,2015)。然而,中国现代化如何持续下去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曹立群,2016;He,2012;张千帆,2011)——我们如何应对转型?(文军、王谦,2017)我们不知道转型何方,是融入世界潮流与世界接轨(Cao and Zhao,2009),还是故步自封?又该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张善根,2018;郑也夫,2002)
二 正视中国社会学面临的问题
其实,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稍有了解的学者就知道,源自西方的各种科技和思想在中国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到清华大学校歌的自白反击“无问西东”,到白话文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第二次解放”(Fung,2010),这样的话题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不断出现在学术界,尽管社会学先贤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根植于本土化的研究(孙本文,2011;吴文藻,2010;费孝通,1997)。
美国社会学并没有任何“统一”的范式或理论,表面看上去甚至有些杂乱无章,而实际上在表面花样翻新的多样性背后,一直凝聚着或者沉淀着两个主要议题:不平等、不公正(Abbott,2018)。主流社会学运用科学的方法论验证理论界提出的种种议题,而公共社会学家、后现代派学人、激进学生把社会学当作朝圣的麦加。只提“美国的范式”而忽视理论下的重大核心议题,是对美国社会学的一个严重误解。反观中国,我们认为社会学的发展如今面临三大问题:大政府(谢宇,2018)、历史包袱和抵赖性文化(a culture of denials)。
大政府带来的问题是复杂的,造成的后果是深远的。比如,在政府掌握大量公权而公权又未受到有效监督的时候,政治关联企业容易获取暴利。政治关联的泛滥以及对利润的追逐不仅仅影响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而且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诱生庞大而失控的政经联盟。在学术界,大政府的后果是,政治浸淫学术,学术与政治勾连,学术研究起起伏伏(Liu and Wang,2015),导致学术不纯粹,偏离学术本应努力的方向。许多明显的学术问题不可碰,很多问题只能研究到某种众所周知的境地,再无法深入下去,即学术有禁区。
除了大政府带来的现实困境,还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带给我们的沉重的历史包袱。费孝通(1997)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要我们在社会学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不仅要重视中西之间的比较,也不要忽视古今的比较。实际上是要我们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和采用“知识考古”的方法来发现当下中国现实的历史文化依据,以更好的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其再三强调,“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费孝通,1997),其目的是“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费孝通,1997),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1997)。“整理故旧”意味着要扬弃糟粕,发掘中国文化中的某些闪光之点,但是决不能以偏概全,全盘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对人性的扼杀、思维的桎梏(文字狱)、民风民情祸乱的传统有所姑息、重新美化。我们决不应该为了保护“悠久文明”的虚荣而全盘接收鱼龙混杂的传统,从而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的时代呼唤与时俱进、“包容开放”的新思维,而不是心灵鸡汤。
抵赖性文化(a culture of denials)也是长期以来束缚学术研究的一股极其顽固的价值流:其中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不能有一说一,而是说一套,做一套。资中筠(2015)洞若观火地感叹:“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费孝通倡导我们要‘文化自觉’,我们对‘西学’也要有‘自觉’的态度:从历史、文化的源头上,从西方思想史的脉络里,乃至从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中,对西方现存的制度文化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和再阐释。相反,面对‘西风’,我们只注重学习其皮毛,而无视其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和本质的东西。”
三 跨国社会学研究
本土化议题是与所谓的“西方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概念。何谓“西方”?我们认为,西方不是拿罗盘就能够找到的,因为西方不是由地理意义上的边界确定的位置,而是一个再造的人文概念(曹立群,2016)。同时它的内涵非常丰富,是具有强烈时间性的文化方面的词,指的是历史的结构和结构化的历史两个方面。历史上,佛教中的西方对欧美人来说是东方。我们如今所说的西方概念,大都起源于地处东欧的希腊。日本位于中国的东部,却是世界上公认的“西方”的一部分。
不可否认,空间、地理、气候会对人的认知产生影响。哈维(Harvey,2000:539)说,空间对大一统的普适性理论有干扰,特定地理和空间中的理解会对理性的认知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不仅要有大理论思路,也必须聆听来自各地,特别是来自底层的微弱声音。厄司(Aas,2012)提出,我们必须质疑是谁在出产理论,谁捷足先登普适,全球化理解的后果是什么。女权学者哈拉韦(Haraway,1988)提出了“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这一概念,认为我们必须潜入社会情境当中,才能够懂得问题的症结所在。情境知识这一概念是客观性的一个方面,既可用于知识的载体,也适用研究的对象。
理论就是一个显微镜片,让我们把现实中的某个特征看得更清楚(曹立群、周愫娴,2004)。我们的味觉不完全是天生的,后天对我们味觉形成的影响常常大于先天。比如酒文化,有人喜欢龙舌兰酒,有人喜欢威士忌,有人喜欢茅台,有人喜欢伏特加。这种多元化的喜欢,其实是地域决定的,而不是先天的。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地域的特质以及这一特质所产生的特殊效果。我们主张用国际视野看待中国研究,把中国的特质与国际视野相结合,“通过‘视界融合’再造有关中国的新的认知模式”(周晓虹,2010)。爱德华·萨义德在他1978年发表的《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东方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由西方人创造出来的非西方世界,是一个他者的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5年,卡里尔编辑了一卷《西方主义》(Carrier,1995),书中的作者注意到,在如何看待对方的问题上,“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带有偏见,对于西方的看法也更为笼统。
对世界精神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希腊,在近代迷失在过往的辉煌中沾沾自喜而无法自拔。虽然希腊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用的几乎所有的政治词汇,但它并没有因为有先进的理念而引领世界。其他欧美国家在希腊的启迪下,丰富了这些理念,完善了对理念的实践,进而引领了工业革命的全球现代化进程。而希腊却一不小心拖了后腿,成为“西方”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希腊的教训是,仅仅有先进的理念是不够的,先进的理念必须在实践中完善,才能创造出现代文明。因此,实践往往与理念一样重要,要知行合一。中国奇迹,摸着石头过河,是从实践开始的,而不是理论。然而,理论的滞后必然要影响实践。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的延续。
在所谓的“西方”知识界,比较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近代,自英国的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培根以来,比较研究也不再是问题。然而,大卫·培黎(Bayley,1996)争辩道,比较研究名不副实,因为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比较”不应该被称为任何学科的下属领域。区分各个下属领域比较研究的,不是比较,而是政治地理,即我们要分析的个案是在一个国家内,还是跨越了两个以上的国家。使用“比较”就会把比较的概念边缘化,也混淆了对科学研究的理解。
当然,我们不是讲“比较研究”这个名词完全不对,而是说“国际研究”这个概念是我们想要提倡的名词。在实践中,国际研究、比较研究、跨国研究是可以互换使用的。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这里的讨论能提高我们准确用词的意识,让大家知道,至少在英文里有这方面的争议。
国际社会学研究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任何跨越两个国家边界的研究。这个定义也有模糊之处,因为许多研究注重某一个国家,却隐含着与另一个国家,或一类国家的比较。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就是这样一本书,把中国的故事讲给德国人和欧洲人听,他必须使用欧洲听众熟悉的概念和事情来把故事讲得更生动。同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是这种非直接的比较,给美国和欧洲的受众讲述中国故事。
我们讲的国际研究,排除以上的间接比较,指两个以上(包括两个国家之间)国家的直接比较。这种研究有三个类型(Kohn,1989):国家作为对象、国家作为环境、国家作为单位。
国家作为对象。研究者主要对某两个国家的某一个现象感兴趣,这种研究可以较深入且具体,既可有质化研究也可有量化研究,美国的“中国研究”中许多研究都属于这一类型(周晓虹,2010)。国家作为环境。学者主要对某一现象感兴趣,想知道这个现象是否在另一类国家里也有相同或者不同的反应。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理论和解释在不同的环境里是否有普遍意义。其所选择的国家是某一类国家的一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最后,国家作为单位主要关心的是某一社会现象是否和国家特质有相关性。这种类型的研究大都属于量化研究,比如张焰和曹立群(Zhang and Cao,2012)有关腐败的研究,赵若辉和曹立群(Zhao and Cao,2010)关于社会变化和迷乱的研究,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当然,在区分不同的研究类型时,各个类型的特点并不总是一目了然,一般情况下,都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叠。
在国际研究中,我们必须依赖科学。科学属于一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是人们追求实用的工具(曹立群、周愫娴,2007)。科学本身不能提供价值,但是科学解决物理方面问题的能力比解决与人类相关问题的能力,更有优越性。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科学有经验主义所有的优点、缺点。社会学中的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都是实证研究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依存,各有千秋,而不是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因此,离不开社会科学的优势与局限。在不同程度上,所有社会学科都必须面临韦伯提出的两个挑战:价值中立与解释性理论。国际研究也不例外,都必须面对这两个挑战(Cao,Sun,and Hebenton,2014)。
四 小结
中国社会学已经初具规模。除了许多能够直接读懂外文原著的学者外,各国社会学经典理论的中文版本如今大都可以得到。中国社会学家也已经人才济济,其中不乏独立思考且思维缜密之人。他们散落在各个高校和科研院所,传播社会学的种子,并时常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本土化”议题有其存在的合理因素,但不是目前中国社会学家最应该关注的议题。作为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中国问题不仅要从本土经验看,更要从周边的国家看,用国际的视野看,而不是满足于闭门造车、弹冠相庆。只有通过反思,社会学才有能力直面大议题。本文响应边燕杰(2017)、周晓虹(2010)提出的本土社会学知识需要国际化的主张,做既扎根中国又能与国际接轨的跨国研究。来自中国的国际社会学必然是内容具体、根植于特定环境中的社会学与全球化社会学的对话。比如,韦伯(2010)在一百多年前声称,对终极困境,西方文化着力于改变现实,印度文化意在逃避现实,而中国文化则强调适应现实。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这个声称能否仍然站住脚跟,有待今天的社会学家来检验。作为一门科学,普遍化的概括、可传播的声称、普适的知识都是社会学理论思维的精髓。跨国研究是确认从一个国家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适用于异地的不可或缺的研究。比较/国际社会学研究,无论是质化的还是量化的,都不比做其他种类的研究更困难、更复杂,也不比做其他种类的研究更科学。
最后,社会学家要研究自己感兴趣、对社会有益的议题,表达自己的“恐惧与期待”;要克尽厥职,担当起社会启蒙的责任(Foucault,1984;资中筠,2015)。现代化的生活是变化的,变化是永恒的,不变是暂时的。现代化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生活选择(贝克和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沃勒斯坦,2006),而每一次选择都面临着不确定,面临着使用有限的理性。因此,我们对生活必须具备更深邃的认知。不要混淆变化与进步的本质区别。社会学理论与研究必须有前瞻性和先验性——我们既要建立一个伟大社会,也要向美好社会(Bellah et al.,1992)迈进。我们应该重视各个学者发出的不同声音,许多社会学家已经走出本土丛林的包围,摆脱了抵赖性文化的束缚,张开臂膀拥抱世界文明,并主动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做研究,无论是跨国研究还是其他研究都不轻松,以有生之涯面对学术的无涯,最终一定能够获得刘禹锡所描绘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的喜悦与满足。
参考文献
边燕杰,2017,《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社会学研究》第5期,第1~14页。
边燕杰、芦强,2014,《阶层再产生与代际资源传递》,《人民论坛》第2期,第20~23页。
曹立群,2016,《重置秩序:法理情——走向法治的中国犯罪学》,《光华法学》第1期,第12~30页。
曹立群、周愫娴,2007,《犯罪学理论与实证》,群众出版社。
费孝通,1997,《反思·对话与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5~22页。
黄仁宇,1997,《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韦伯,马克斯,2010,《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秦晖,2008,《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585.html。
孙本文,2011,《当代中国社会学》(下编),商务印书馆。
文军、王谦,2017,《从发展社会学到转型社会学》,《江海学刊》第1期,第96~104页。
贝克,乌尔里希、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文藻,2010,《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
谢宇,2015,《中国的不平等到底有多严重?》,在浙江大学的演讲,杭州。
谢宇,2018,《走出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1~13页。
杨国枢,2004,《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叶启政,2006,《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沃勒斯坦,伊曼纽尔,2006,《知识的不确定性》,王昺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张千帆,2011,《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领导者》第42期。
张善根,2018,《法律信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张焰、曹立群,2012,《社会支持理论与腐败:影响腐败的结构性决定因素的再检验》,《青少年犯罪问题》第2期,第20~30页。
郑也夫,2002,《中国的信任危机》,《新闻周刊》第20期,第68~69页。
周晓虹,2010,《“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学术月刊》第9期,第5~13页。
资中筠,2015,《为什么我们需要再启蒙》,《党政视野》第3期,第68~68页。
Aas,Katja F.2012.“‘The Earth is One but the World is not’:Criminological Theory and its Geographical Divisions.”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16(1):5-20.
Abbott,Andrew.2018.“Varieties of Normative Inquiry:Moral Alternatives to Politicization in Sociology.”American Sociologist 49(2):158-180.
Bayley,David H.1996.“Policing:The World Stage.”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Education 7(2):241-251.
Bellah,Robert et al.1992.The Good Society.NY:Vintage Books.
Cao,Liqun and Shanyang Zhao.2009.“The Great Convergenc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w century.”Sociological Focus 42(3):222-227.
Cao,Liqun and Yisheng Dai.2001.“Inequality and Crime in China.”In Crime and Social Control in a Changing China,edited by Jianhong Liu,Lening Zhang,and Steven E.Messner,pp.73-85.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
Cao,Liqun,Ivan Y.Sun and Bill Hebenton.2014.“Introduction:Discovering and Making Criminology in China.”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Criminology,edited by Liqun Cao,Ivan Y.Sun,and Bill Hebenton,pp.xvi-xxvii.London:Routledge.
Carrier,James G.,ed.1995.Occidentalism:Images of the West.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Michel.1984.“What is Enlightenment?” pp.32-50 In The Foucault Reader,edited by Paul Rabinow,pp.32-50.New York:Pantheon Books.
Fung,S.K.Fung.2010.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Anthony.1990.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UK:Polity Press.
Habermas,Jürgen.1987.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welve Lectures.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Cambridge UK:Polity Press.
Haraway,Donna.1988.“Situated Knowledges: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3):575-599.
Harvey,David.2000.“Cosmopolitanism and the Banality of Geographical Evils.”Public Culture 21(2):529-564.
He,Weifang.2012.In the Name of Justice:Striving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New York:Brookings Institution.
Kohn,Melvin,ed.1989.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Newbury Park,CA:Sage.
Liu,Sida and Zhizhou Wang.2015.“The Fall and Rise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11:373-394.
Said,Edward.1978.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
Zhao,Ruohui and Liqun Cao.2010.“Social Change and Anomie—A Cross-national Study.” Social Forces 88(3):1209-1229.
[1]曹立群,加拿大安大略省科技大学社会人文学院终身教授;杜少臣,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