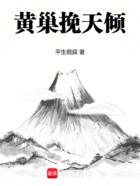
第12章 君臣一心(求月票 求推荐票)
“再等等。”
仇士良懒懒地抬起三根手指,绣着金线蟒纹的袖口,疑似在烛火下吐出了蛇信。
立时有手下上前,用铁钩刺啦一声,撕开粘连在男子口鼻处的湿纸。
那人胸腔剧烈起伏着,被水泡得发白的嘴唇使劲翕张:
“是侍郎大人……那夜秘密拜会我家家主的,是礼部侍郎大人……”
“说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不记得……”
仇士良忽然俯身,捻起案头一块浸透的桑皮,慢条斯理地往男子青紫的脖颈上贴。
“说是要在殿试上对付您!”
仇士良毫无意外地点点头,将整沓湿纸摁在男子脸上,浑浊的笑声从他喉间溢出:
“李台郎,我就知道是你。”
田录瞥见干爹抚弄玉扳指的细微动作,心里瞬间明白,这是打算留活口的意思。
当然,要留下的并非李德裕府上的这名仆人。
而是黄巢。
“卷子拿给我看看。”
田录赶忙双手将黄巢的殿试考卷,递到仇士良面前。
仇士良展开卷子,目光扫到卷尾的两首诗时,不禁微微一怔,脸上浮现出一丝难得的震惊之色:
“好诗才!”
邱慕阳眼中也闪过一抹讶异,不过他生性冷淡,很快便恢复了平静。
仇士良看着田录,开口问道:
“慕阳排第几?”
田录在一沓殿试卷中翻找起来,好不容易才从倒数后七张找到。
仇士良见状,忍不住低声骂了几句礼部那些文官。
随后大手一挥,将邱慕阳的考卷挪到了最上方,沉声道:
“就第十名了。”
转头望向垂手侍立的青年时,面上又浮起几分惋惜:
“可惜了,若非身份泄露,便是殿试前三甲也未必不可。”
邱慕阳恭敬应道:
“大父之恩,没齿难忘,孙儿不敢再有他求。”
仇士良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抬手轻轻拍了拍邱慕阳的肩膀。
而后转头看向田录,吩咐道:
“你先过去,我晚半个时辰再去面圣。”
于是,宦官们捧着黄绸包裹的考卷鱼贯而出。
只留下殿角那具遭受水刑的尸体,在烛影中愈显青白。
寝宫内。
李炎正对着冷透的晚膳出神。
自登基以来,他总要等暮鼓敲过三巡才肯用膳。
唯有看着宫门次第落锁,听着更漏声在空荡的殿宇间回响,才能稍缓心中焦灼。
皇帝的位置,本应属于他的侄儿李成美。
李成美是唐敬宗李湛的第六子,因先帝文宗子嗣凋零,庄恪太子暴薨后,李成美才被选为太子。
册封新太子的当天,唐文宗突然病倒,册封仪式被迫取消。
仇士良趁着先帝病重,假传圣旨,将李炎立为皇太弟,顺利将他推上皇位。
明面上,李炎自然不会承认圣旨是假传的——
谁会与皇位过不去呢?
背地里,他心知肚明,仇士良废黜李成美,选择自己继位,不过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量。
宦官集团的权力,向来依赖于对皇帝的控制。
若李成美登基,没有拥立之功的仇士良,很可能被新皇帝边缘化。
只可惜,仇士良算错了一步。
李炎不仅比那个侄儿更有能力,心思也更为深沉。
他隐忍不发,不过是在积蓄力量,等待中兴李唐的时机。
在那之前,他必须对仇士良以安抚为主。
因此,在昨日的殿试上,他才会接受仇士良三言两语的托词,将那桩科举弊案轻描淡写地化于无形。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待朕重掌军营……”
李炎心中默念,目光渐冷。
恰在此时,寝殿外传来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
李炎神色恢复如常,若无其事地拿起汤勺,舀起羹汤,缓缓送入口中。
田录轻手轻脚地走进殿内,恭恭敬敬地行了大礼,而后双手高高举起手中的黄绸包裹:
“圣上,礼部诸位大人已阅完殿试卷子了。”
李炎眉梢微微一挑,不紧不慢地问道:
“怎么去了这么久?”
田录赶忙上前一步,躬身回道:
“回圣上的话,奴才过去的时候,南院正吵得不可开交。崔侍郎甚至扬言,明日早朝要弹劾李大人独断专权。”
“哦?”
李炎拿着汤匙的手微微一顿,追问道:
“可是为了那两人的名次?”
“圣上英明,正是此事。”
李炎继续慢条斯理地吃着饭,淡淡追问道:
“结果如何?”
“邱公子与那黄巢,都排进了前二十。”
“有意思。”
李炎嘴角泛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
“放书案上吧。”
待田录应了一声,悄然退下。
李炎瞬间没了胃口,放下碗筷,大步走到书案前,展开试卷查阅起来。
“第一,卢锦程。”
“第二,王沐霖。”
“第三,崔知睿。”
“第四,李靖澜……”
一页页翻下去,李炎面色愈发阴沉。
众所周知,“五姓七望”指的不是五加七,共计十二个大族;
而是代指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以及太原王氏,这七个大族。
在他们之下,便是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等同样声名赫赫的高门士族;
以及在地方上拥有一定势力根基的中等世家,和处于鄙视链底层的普通士族,可称“寒门”。
这些世家大族,宛如一张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巨网,牢牢把持着大唐的官僚系统。
对于天然追求集权的封建帝王而言,这种局面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延续科举制的初衷,便是唐朝皇帝试图将选官权力收归中央,打破世家对仕途的垄断,进而削弱世家势力。
而当下的大唐,却犹如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重疴缠身。
藩镇割据,宦官干政,皇帝的权威被肆意践踏。
李炎急需世家支持,才会听取杨钦义的建议,选择出身赵郡李氏的李德裕入朝为相。
李炎的眼中闪过一丝不甘与无奈。
若非局势如此艰难,他恨不得立刻将排在前几的世家子弟通通后挪。
“邱慕阳,第十名么?”
李炎稍作思忖,轻轻翻过这一页,默认了此人的成绩。
从第十一名开始,他全神贯注地阅起卷来,手中的笔不时在试卷上批注几句。
没过多时,黄巢的试卷便呈现在他眼前。
初看之下,李炎发现黄巢前面几道题的作答,表面看似中规中矩,实则暗藏玄机,仿佛有某种新奇的见解呼之欲出。
李炎联想到黄巢在宣政殿上刚正不阿,当着仇士良的面告发其孙子的场景,满意道:
“黄士子德才兼备,如此排名,实至名归。”
他原本以为,主考官李景让会出于上述之事,黜落这个让他遭受贬谪的青年人。
事实却出乎李炎的意料。
李景让依旧秉持公心,甚至还愿意为此人与同僚据理力争。
李炎刚想脱口夸赞一句“肱股之臣”,可一翻页,那首《石灰吟赠乐和李公》便映入眼帘,不禁勃然色变。
又待他读完全诗,疑虑再次消散,转而重新认可了李景让的做法,感叹道:
“借物喻人,表意深刻,此首诗作堪称本届殿试第一。”
但当李炎继续往下,读完黄巢所作的第二首《会昌杂诗》时。
整个人猛地一震,仿佛被一道惊雷劈中。
许久之后,他才发觉,自己已然单手支撑书案,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
“九州生气恃风雷。”
如今的大唐藩镇割据,犹如一盘散沙,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不听中央号令;
李炎急需一场如诗中所言的风雷变革,来打破这改朝换代的僵局,重新凝聚九州人心。
“万马齐喑究可哀。”
朝堂之上,宦官干政,有识之士难以发声,有志之士被打压排挤,整个朝廷宛如一潭死水——
不正是诗中所描述的,万马齐喑的悲哀景象吗?
“我劝天公重抖擞。”
李炎代入天公,想到自己虽贵为天子,但在中兴大唐的路上举步维艰。
这句诗无疑是在敦促他,身为大唐的天子,要重新振作起来,冲破重重阻碍。
“不拘一格降人才。”
选官制度被世家把控,寒门子弟难有出头之日。
国家要想重振雄风,就必须广纳贤才,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应给予机会。
“好一个一语双关……既是在谏朕,也是在自荐啊!”
李炎心潮澎湃,连胃口都好了不少。
他带着黄巢的考卷,重新回到餐桌前,一边享用晚膳,一边细细品读黄巢的诗文。
等到酒足饭饱,李炎已然有了决断。
“黄巢忠君忧国,富有才学,将他擢升至第三人,以表勉励。”
大唐年间,殿试第二名与第三名统称榜眼。
虽然“探花”这一称谓已经出现,但它并不特指科举考试的第三名;
而是指在宴席活动中,选取同榜最俊秀的二三名进士,作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探采名花。
等到后世,殿试成为定制,朝廷才会敲定“探花”之名。
就在李炎为黄巢的才学感到欣慰,准备下旨时,殿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李炎抬头一看,只见仇士良垂首低眉,小步走了进来,顿时暗道不妙。
直觉告诉他,仇士良入夜前来,极有可能是为了黜落黄巢。
毕竟,黄巢不久前狠狠打了仇家人的脸面,又怎会轻易放过此事。
但李炎毕竟是久经世故的帝王,面上洋溢着出笑容,迎上前去,主动拉住仇士良的手。
“仇将军来得正好,快快入座,同朕共用晚膳。”
“圣上厚爱,老臣实在惶恐。”
仇士良忙不迭地谢完恩,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音带着几分颤抖说道:
“其实,老臣今夜冒昧前来,是想再为我那不孝孙儿伪造解牒一事,向圣上请罪。”
李炎微微一怔,旋即再次浮现出温和的笑意,上前一步,双手扶起仇士良:
“此事朕不是已经知晓了吗?你并无罪过。
“况且,你的‘不孝孙儿’很是争气,朕决定点他作今科第十。”
“这,这如何使得……”
仇士良浑浊的眼眸中,顿时闪过几分难以置信。
他双膝一软,重重跪地,额头撞击青砖发出沉闷声响:
“老奴……老奴纵是粉身碎骨,也难报圣上隆恩!”
李炎凝视着仇士良微微发颤的身躯,心中暗自思量:
‘神情不似作伪,看来仇士良确未染指礼部。’
更何况,派去取卷的田录,是他自颍王府带进宫的老人,忠心可鉴。
仇士良纵有通天手段,也难在阅卷上做手脚。
念及此处,李炎紧绷的心弦略松,伸手虚扶道:
“将军言重了。若无将军鼎力相助,何来今日的朕?”
他顿了顿,语气愈发温和:
“朕信得过将军,更信得过仇家。待放榜之后,便让慕阳改回本名吧。”
仇士良闻言,第三次叩首谢恩。
在李炎的坚持下,他才战战兢兢地虚坐在座旁,执壶为皇帝添茶。
茶香氤氲间,他状似无意地瞥见李炎手边的考卷,故作惊讶道:
“咦,圣上,这莫不是那黄士子的考卷?老臣可否一观?”
李炎执箸的手指微微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仇士良双手恭敬地捧过考卷,细细品读。
待看到最后两首诗文时,也如李炎一般惊叹连连,甚至还将黄巢比作大李杜再世。
“敢问圣上,给黄巢的是何名次?”
‘还是来了。’
李炎闭眼一瞬,心知殿试第三的位置,已经无法给到黄巢。
为了稳住仇士良,让这老家伙相信自己并无铲除阉党之心,稳妥之计,是将黄巢置于二十名开外。
可“重抖擞”三字,始终在李炎脑海里久久不散,让他不愿放弃这么个铮铮铁骨的俊才。
沉默半晌,李炎强扯出一抹笑容:
“此人尚不堪大用,礼部斟酌之后,勉强给了个双十名次。”
果然,仇士良听到这话,轻轻摇了摇头,露出明显反对的神色。
李炎见状,双手不自觉地在膝上紧握成拳,强忍着不发作。
却听仇士良缓缓开口:
“黄士子诗赋绝伦,文采斐然,远胜五姓七望中的那些翘楚……”
这位久经宦海、在权力漩涡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人,脸上露出一抹让李炎捉摸不透的微笑,一字一字地道:
“当冠以状元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