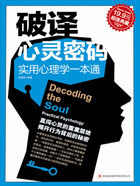
心理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各学派争锋
文艺复兴是一场发生在14世纪末至17世纪的思想文化运动,发源于意大利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佛罗伦萨,后来蔓延到欧洲各国。在这个时期,人们对神的信仰开始动摇,提倡人性,反对神性。因此,这个时期的成就为17世纪至18世纪的心理学研究准备了条件。
史上最睿智的人达·芬奇
文艺复兴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它是新兴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来宣传人文精神,在知识、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引发了革命。
在思想上,其复兴的对象有两个。
复兴的对象之一就是毕达哥拉斯主义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认为神流出理性,理性流出灵魂,灵魂则流出物质世界,这就是有名的“泛神论”,即认为神在万物中,万物在神中。这种观点具有极强的神秘主义色彩,却同时显露出非常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所以泛神论成了这个时期人们摆脱有神论的一种很方便的过渡形式。
复兴的对象之二就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所谓自然哲学,是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的一种探讨宇宙本源的哲学,到了17世纪,这种哲学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而且企图代替自然科学的哲学。这个时期的达·芬奇就试图复兴赫拉克利特等人的唯物主义感觉论。
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被视为整个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他是一位真正的天才,除绘画之外,在众多科学领域都有研究成果。比如他热衷于解剖学,在无数次用青蛙进行解剖实验之后,他终于发现青蛙就算被切掉头或者摘除内脏甚至是心脏之后,都还能够活几小时,但是如果用尖锐物刺穿它的脊髓,它就会当场毙命。通过他的解剖,人们才发现了脊髓对维持生命体有着重要作用。

达·芬奇一生反对神学和迷信,推崇科学真理。据说有一次,他独自到山上找灵感,结果在山里迷了路,最后走到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前。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曾经这样描述:“我突然产生了两种情绪,一种是害怕,一种是渴望。面对漆黑的洞穴是感到很害怕,但害怕的背后却藏着渴望,我真的很想看看在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怪异的东西。”这其实是困扰他一生的矛盾情绪,对于生活的不可知以及不可预见性,他感到害怕。但越是害怕,就越想去探究这种神秘的不可知,想要将其加以研究解释,透析其真谛。
达·芬奇对于视觉感官及其功能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眼睛是其他一切感觉器官的统治者,是灵魂的窗户,所以灵魂非常害怕失去眼睛。面对突然来临的危险之时,人们下意识的反应是抬起双手掩住眼睛,这其实是灵魂想要受到保护的本能需要。这种看法刚好符合了我们现在所说的防御反应以及反射原理的实质。
达·芬奇还对知觉颇有研究。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真正研究并细致描述过知觉。达·芬奇对制约知觉的条件的描述出现在他的《论绘画》手稿当中,这其中的许多关于绘画的原理和技巧都被现代心理学所采用。他指出对人产生距离知觉的影响因素有五个。
第一为线条透视,看到的物体离眼睛越远,视角就会越小。
第二为节目透视,就是说物体离得越远,就越难以看清楚细节。
第三为空气透视,当我们观察天空的时候,会发现越远越蓝,那是因为空气、烟、雾共同影响的结果。
第四为移动透视,当我们注视近处的物体时,如果我们的头左右摆动,会感觉看见的物体也随着头同向移动;但是如果注视的是远处的物体,我们摆动头部时,就会感觉物体与头部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
第五为双眼视差,就是左右眼对看见的同一个物体所产生的感受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人文主义与各家理论
文艺复兴时期的心理学思想呈现了多元化的局面,其理论形式也各不相同。
早在古希腊就已经萌芽的物活论在这个时期成了心理学的理论形式之一。物活论是一种万物有生论,其核心思想是认为所有物体都具有生命和精神活动的能力。
除了物活论之外,还有感觉论,它强调所有认识都来源于感觉。在意大利自然哲学家特莱肖(1509~1588)的观念里,所有东西都来自于感觉经验。打个比方,当我们感觉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不会同时把它感觉成另外一种东西。
另外,这个时期还存在机械论的倾向。支持人文主义的人都趋向于用机械论的图式来描绘人的心理活动的机制。达·芬奇就首先肯定了力学决定论的长处,因为这个理论否定了灵魂能够解释一切的原则。他希望能够从物质的角度出发,把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用一种统一的模式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