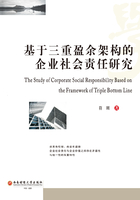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述评
第一节 国外研究进展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及内容
“企业社会责任”一词自1924年第一次被谢尔顿提出来后,围绕其定义和内容的研究不计其数。但由于学者们研究的阶段背景和角度各异,大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界定。
早期的学者主要是基于伦理观和道德观的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定义,被誉为“公司社会责任之父”的美国学者Howard Bowen,于1953年在其所著的《商人的社会责任》中,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要依照整个社会的目标与价值观来进行经营决策及活动。尽管这个定义比较宽泛且具有模糊性,但它促使了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理性研究,而不是仅停留在感性认识与评价上。K. Davis(1960a)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施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决策与行为,但这些决策与行为不是出于经济性及技术性的目的。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戴维斯原则”,即社会责任刚性原则,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须符合其社会能力,量力而行。后来,K. Davis(1973b)更详细地解释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是道德的约束和舆论的压力,企业社会责任是这样一种行为,它是出于社会利益角度的考虑,且在法律要求之外。但是早期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都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其理解具有广泛性,直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被普遍认可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和内容。R. Edward Freeman(1984)![FREEMAN R E. Strategic planning: a stakeholder approach [M]. Boston: Pitman Press, 1984](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40301F/165086806059532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68193-FtjyA335trq4hzKtjhXTCqIbdi9ztUuC-0-e498b701fa01b5ded6651d306a5dddb8) 率先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明确回答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对象问题及相应责任。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对任何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集团承担的责任。这就给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思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现了两种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代表性学说,一种是“四成分责任说”,另一种是“三重底线责任说”。
率先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明确回答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对象问题及相应责任。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对任何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集团承担的责任。这就给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思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现了两种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代表性学说,一种是“四成分责任说”,另一种是“三重底线责任说”。
“四成分责任说”是指完整的企业责任从低到高排列应当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四种责任(Archei B. Carroll, 1979)。Wartick和Cochran(1985)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其他责任,并将这四种责任以金字塔的形式表现出来。金字塔模型不仅提出了这四种责任,还表明了金字塔底层是经济责任,经济责任仍然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基于四种成分责任说,欧盟在2001年的绿皮书中就企业社会责任明确提出,企业应该在自愿的基础上,在日常运营和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中综合考虑社会和环境问题。企业社会责任意味着不仅要满足法律要求,还要在人力资本、环境和利益相关者关系上投入更多(Maria-Teresa Spezialea、Lina Kloviene, 2014)。有研究表明,顾客光顾、政府支持、风险管理、有能力员工的保留和成本削减是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动因(Brine Matthew、Brown Rebecca、Hackett Greg, 2007)。一些公司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好的商业机会的来源,另一些则认为它是一种好的商业实践(Nikolaos A. Panayiotou等,2009)。因为企业充分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是把追求社会效益作为一个长期目标,并且将其看作法律或者经济上要求的一种义务,是企业必须履行的责任,企业必须做出负责任的、符合道德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行为,并且对它的利益相关者保持透明(Nikolaos A. Panayiotou等,2009)。这些都是基于“四成分责任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解。
另一种学说是“三重底线责任说”,是指企业必须履行的最基本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这三方面的底线(John Elkington, 1997)。就责任领域而言,经济责任是传统的企业责任,主要表现为提高利润、纳税和股东分红;环境责任就是保护环境;社会责任就是对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企业应当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转向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整体目标的最大化。基于三重底线责任说,澳大利亚国会联合委员会公司和金融服务部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为,公司应当考虑其活动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管理这些行为以使其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中达到平衡(Yusuf Ibrahim Karaye、Zuaini Ishak、Noriah Che-Adam, 2014)。现代企业被鼓励去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因为这不仅仅是企业的一个机会,在更多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是顾客、雇员、社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期望(Mark-Herbert、Cecilia、Von Schantz、Carolina, 2007)。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能让企业被认为是富有责任心的、值得信任的,是一个能够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信任的有效管理工具(Dra. Belén Fernández-Feijóo Souto, 2009)。
可见,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两种代表性学说得到了监管者、学者、企业的广泛认可。
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
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主要是描述了一种现象,却没有就如何面对这种挑战提出指导(Alexander Dahlsrud, 2006),正是由于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其评价也变得相当困难。国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方法、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模式的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方法主要有年报内容分析法、污染指数的测量法、问卷调查法、声誉指数法、专业机构数据库法(王昶、周登、Shawn P. Daly, 2012)。Elena Avram和Silvia Avasilcai(2014)运用综合比较分析法对全球报告倡议(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简称GRI)、资源观倡议(Resource Based View Initiative,简称RBVI)、全球环境管理倡议(Glob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itiative,简称GEMI)的优劣势进行比较分析后,提出用平衡计分卡模型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可以在不影响上述三个模型最初目的的情况下,运用以上所有指标,对企业做出全面评价。
基于全面和系统的建模方法,在一个企业战略规划系统中利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用企业社会责任系数来表达一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不管在国际层面、国家层面还是社区水平上,该系数都能够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价,但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测量和比较标准(Gopal K. Kanji、Parvesh K. Chopra, 2010)。虽然大量研究都提出和构建了在某个方面或从某一个维度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模型,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满意地衡量一个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没有任何研究解释企业社会责任和区域层面上的其他重要企业战略变量的因果关系(Qi Wang、Chong Wu、Yang Sun, 2015)。
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分为财务计量、非财务计量和提前指标、滞后指标(Marika Arena、Michela Arnaboldi, 2014)。会计计量是绩效报告的关键。非财务计量旨在监督企业的长期成功因素,比如顾客满意度、企业效率、人力资源、创新力等(Maria-Teresa Spezialea、Lina Kloviene, 2014)。75家上市公司的GRI报告在采用结构化的内容分析法后显示,在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中最受关注的是劳工关系和工作条件,能够量化的指标比其他无法量化的指标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分数(Lujie Chen、Andreas Feldmann、Ou Tang, 2014)。通过研究文献发现,在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中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的结合是必要的,其目的主要是确认企业内外部流程的关键信息被理解和计量(Maria-Teresa Spezialea、Lina Klovie, 2014),如果非财务计量指标设计得当,利益相关者便能够从这些指标中察觉到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的微弱信号(Marika Arena、Michela Arn-aboldi, 2014),从而及时地了解企业现状,做出投资决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公司财务绩效(用托宾Q值衡量)是成正比关系的,但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公司日常运营绩效(用资产回报率衡量)的关系,在有的企业中是负相关的(Wolfgang Drobetz、Andreas Merikas、Anna Merika、Mike G. Tsio-nas, 2014)。平衡记分卡可以帮助定义和控制提前—滞后指标的混合使用,即财务绩效、客户服务、业务流程和企业发展指标,而GRI报告能够选出企业战略计量指标,结合平衡记分卡模型和GRI报告则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发展战略中(Nikolaos A. Panayiotou等,2009)。
三、三重盈余的研究
自1997年“三重盈余”被首次提出后,1999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发布了第一个基于三重盈余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2000年发布了正式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并于2002年进行了修订,称为G2(温素彬,2009)。GRI在2006年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第三版,简称G3。G3采用可持续发展的“三重底线”理念,将指标分为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层面,规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谢良安,2009)。鉴于GRI只是一种由企业自愿选择的指标系统,国外学者对其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旨在不断提高GRI指标的可操作性和权威性。
G3不仅在学术上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肯定,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的机构和媒体已迫使企业进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披露。比如,美国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oxic Telease Inventory)要求排放超过一定限值的化学物质必须要报告;在荷兰,一些要求公司自愿披露环境责任的相关法规也是被支持的。
国外学者对三重盈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三重盈余概念进行新的解读、分析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报告的优势、G3指标的适应性和普遍性研究以及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式应用型研究四个方面。
对三重盈余概念进行新的解读,能够增强其普遍性和适用性。虽然现在度量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标准以及大量分散风险的战略都在不断发展,但是分析主要集中在对经济、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单独影响(Sneddon, 2006),并没有提出一个领域的改善会对另一个领域造成什么样的具体影响(促进或者阻碍)及其影响程度。将制度约束与三重盈余的三个方面看成一个“四面体”,当且仅当四个方面共同进步时才能让整个四面体实现可持续发展(Martin O'Connor, 2006)。也有学者从三维的角度对“三重盈余”进行了重新解读,把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式作为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种通用方法后,这种三维解读可以作为该方法的核心原则(Wynn Chi Nguyen Cam, 2013)。
有的学者认为会计实务需要的就是能有效地应用于无形和主观元素的量化的标准,比如在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方面,但是如果依然将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的使命,那么只能运用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式来衡量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此让所有企业利益相关者都一致地认为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与经济绩效同样重要(Oakley、Buckland, 2004)。使用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报告能为一个企业带来五类收益,即成本收益、节约营运成本、提升品牌价值、提高市场知名度以及拉近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能够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嵌入企业战略(N. M. P. Bocken等,2014)。成功的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报告能够使企业组织结构更加明朗化,能够让所有利益相关者看到该企业计划未来在经济绩效、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改善(A. George Assaf, 2012)。越大的企业进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活动越多,中小企业没有太大的压力去从事这些活动,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是微乎其微(Cristina Gimenez, 2012)。
虽然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式对于可持续发展在概念上是相当新的,但是在行业量化和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可比较性这两方面始终存在问题。因为每个行业都是一个需要用特定参数来表现的复杂的系统,都需要单独分析其中的个体和整个行业(Sneddon等,2006)。也就是说,虽然G3发布了很多指标,给各个公司提供了一个基于三重盈余的绩效评价模式的指南,但是它的适用性和普遍性仍有待提高。比如,在加拿大94家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指标中,我们发现G3指标虽然被很多公司采用,却无法作为一个通用的标准(Laurence Clément Roca, 2011)。基于三重盈余的G3指标,虽然给公司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绩效评价方式,但是它要成为普遍试用的指标还存在困难。比如说,在接受调查的94家公司之中,47.9%的公司运用了G3中的指标来进行可持续发展报告,但是其中只有31家公司运用了自己特定的经过修订的指标,各个行业运用的指标也不尽相同(Laurence Clément Roca, 2011)。
大多数关于三重盈余的研究不再处于初级和选择评价指标的阶段,而是逐渐在改进,特别是单一地研究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式的学者越来越少,他们逐渐倾向于实际应用性的研究。如Amy L. Bergenwall(2010)将三重盈余和丰田生产模式相结合来探讨基于三重盈余的标准和在可持续性发展条件下,不同的丰田生产模式设计对企业产生的影响。Cristina Gimenez(2012)分析加工行业之后,得到从事社会责任和环境活动能够使企业获得经济效益,进行供应链评估对三重盈余绩效没有影响,但是进行供应链合作却能够改善三重盈余绩效评价结果的结论。A. George Assaf(2012)以旅馆行业作为实证研究,运用了统计假设检验方法,证明旅馆财务、环境和社会责任报告水平的提高对企业绩效具有重大的影响。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式的可比较性和可量化性在应用中始终存在一些问题,虽然有学者证明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行业标准所占比重的变化对评价公司的名次几乎不会产生影响(Carlos Eduardo Durange de C. Infante, 2012),但是贝叶斯网络和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式相结合形成的可持续发展记分卡,就能够作为一个解决全球层面仅仅运用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式的问题的工具。以澳大利亚乳制品行业为例,试验积分卡的结果表明,这种结合的积分卡可以修订为有地方特色的评价工具(L. Buys, 2014),这就为以后的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国外的研究已经进入如何提高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式的普遍应用性的研究阶段,主要研究都集中在分析三重盈余在各个行业的适用性和特定性上,有进行实证研究也有进行理论研究。如对于供应链管理,可以用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管理对三重盈余绩效评价模型进行补充。Stefan Gold(2011)和K. Devika(2014)等学者则以玻璃行业为例,分析了如何设计一个基于三重盈余的供应链网络。有的学者则分析企业的活动可能对三重盈余绩效评价结果产生的影响,如Cristina Gimenez(2012)利用企业内外部活动来分析了企业的三重盈余绩效。
四、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
(一)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随着生态学家的抱怨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担忧日益增加,结合1987年联合国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西方部分企业开始单独披露环境和社会报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应运而生。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是由美国对环境负责经济体联盟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倡议的非政府组织,是为了帮助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理解和交流关键的可持续性问题(比如气候变化、人权等),其使命是制订、完善和推广一套可持续发展标准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网络,帮助全球决策者做出让经济和世界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决策。
为了提高可持续发展报告所披露信息的实用性和可比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在2000年发布第一版《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简称G1),是全球第一个关于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三重底线”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框架;2002年发布第二版《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简称G2);2006年进一步修改和发布第三版《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简称G3)。G3融合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原则,让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对投资者和分析师更有价值,相比G2, G3更加简单实用,能够帮助机构聚焦于实质性的问题,改善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崔征.解读第三代《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J]. WTO经济导刊,2006(11):90-91](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40301F/165086806059532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268193-FtjyA335trq4hzKtjhXTCqIbdi9ztUuC-0-e498b701fa01b5ded6651d306a5dddb8) 。2011年发布了G3.1,相对于G3而言,G3.1增加了有关人权、性别和社区方面的报告指引。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指导下,过去的20年中,企业披露的环境报告和社会报告等单独类型的报告已经逐渐被整合成综合性报告,公开披露企业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责任。2013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发布了第四版《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简称G4),意味着可持续发展报告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报告的发布者和使用者都意义非凡。
。2011年发布了G3.1,相对于G3而言,G3.1增加了有关人权、性别和社区方面的报告指引。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指导下,过去的20年中,企业披露的环境报告和社会报告等单独类型的报告已经逐渐被整合成综合性报告,公开披露企业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责任。2013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发布了第四版《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简称G4),意味着可持续发展报告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报告的发布者和使用者都意义非凡。
(二)G4主要内容
G4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说明G4的原则,以及组织使用G4时所应注意的前后关联性、规则、摘要信息等。第二部分为执行手册,包含了指南中的重要议题,作为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世界性标准,G4指明了组织应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报告。G4对G3.1核心的、原则性的内容均有所保留,如报告内容界定的原则和质量界定的原则。G4将标准披露分为常规标准披露和分类标准披露两部分,并提供了相应的披露指标及披露指导,鼓励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布者在与利益相关者保持沟通的前提下,可以不用公布所有信息,而只披露与其核心业务有关的内容。
G4的第二部分“标准披露”规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报告格式和报告内容。GRI可持续发展报告主要由战略与概况和绩效指标两部分构成。G4要求机构从四个方面披露其战略与概况的情况,即战略与分析,机构简介,报告规范,管治、承诺与参与度。每个方面都通过报告要素规定了具体的披露内容,共42个报告要素。当然,报告机构通过应用上述的报告原则,可以对报告要素进行选择。通过这部分披露,机构可以展现其整体背景,有助于报告使用者了解机构的战略概况以及公司治理等信息。
GRI所界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集中于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层面。因此,G4要求机构分别从这三个层面来披露其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绩效情况,并且每个层面都通过绩效指标规定了具体的披露内容。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层面,是指机构对利益相关者的经济状况以及对当地、全国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9个指标分别从经济绩效、市场占有率、间接经济影响3个角度来反映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金流动以及对社会的主要经济影响,从而反映出机构对更大范围的经济体系可持续发展所做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层面,是指机构对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自然系统(包括生态系统、土地、空气和水)的影响。在经济、环境与社会三类指标中,环境指标得到最为广泛的重视。这类指标既包括量化指标,如吨、千克、焦耳等,也包括说明性的非量化指标,如减低产品与服务对于环境的影响的计划及其成效等。30个指标从9个角度(即物料,能源,水,生物多样性,排放物、污水及废弃物,产品与服务,违规事项,交通运输以及整体情况)来反映了报告机构对环境的影响。其中,排放物、污水及废弃物一个角度就占了10个指标,说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对这类事项的重视程度。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层面,是指机构对其所处的社会体制的影响。40个指标分别从四个方面、22个角度进行了报告。第一方面为“劳工措施与合理工作”,包括雇用、劳资关系、职业健康与安全、培训与教育、多元化与平等机会5个角度、14个指标。这些指标主要是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等国际公认的标准制订的。第二方面为“人权”,包括投资及采购、非歧视、结社自由与集体议价权、童工、强制劳动与强迫劳动、保安雇员、本地雇员权利7个角度、9个指标,主要反映机构如何尊重与帮助维持个人的基本权利。第三方面为“社会”,包括社区、贿赂、公共政策、反竞争行为、遵守法规5个角度、8个指标。这些指标主要反映机构活动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以及与其他社会组织互动时可能出现的风险。第四方面为“产品责任”,主要反映机构的产品与服务对消费者的直接影响,包括消费者健康与安全、产品与服务、市场营销、客户隐私权、遵守法规5个角度、9个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