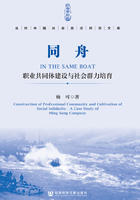
第二节 文献述评
为了讨论民生公司在企业组织框架下建设和维护职业共同体的努力,需要回顾几种相关的思想脉络与理论资源,为讨论提供一个基本的历史话语背景和概念框架。下面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介绍清末民国时期知识界对中国内部组织性的认识、对“群”的讨论与培育群力的主张;再进入社会学的学科话语中,介绍职业团体研究的传统以及劳工社会学所开创的工厂民族志研究传统和经典的劳工调查;最后进入具体的民生公司研究,对已有的民生公司研究进行评述。
(一)清末以来知识界的有关“群”之讨论与培育“群力”主张
自甲午战争失利以来,诸多时贤在与西方的对比中思考中国的问题所在,一致认为中国落后的根基在于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具有明确的组织性,“实在是一盘散沙”(孙中山,1924),“在社会组织上的问题是上下不通的;政府动员能力的微弱,由‘家’组成‘国’机制的松散,促使士大夫思考把个人、家庭、国家三个层次紧密结合的办法”(金观涛、刘青峰,2001)。由此,改变中国弱败局面的根本办法落脚在“合群”之上,一时各种合群之论蜂起,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等人均就“群”与“合群之道”发表宏论。
严复是公认的引进“群学”的第一人(李培林,2008:28),也是他最先将“群”从古代典籍中借用过来指涉西文里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society”的概念。严复所译介的群学观点,乃直接取自英国早期实用主义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著作。“而又有锡朋塞(即斯宾塞——引者注)者,亦英产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刘梦溪,1996:541)。严复认为,“民生有群”,群有数等,其中组织程度最高的“有法之群”即社会(姚纯安,2006:108)。也就是说,当群居之民有了共同遵守的约定和共同的利益、建立共同认可的长期不变的制度时,才可以称为“社会”。“偶合之众虽多,不为社会。萍若而合,絮若而散,无公认之达义,无同求之幸福,经制不立,无典籍载记之流传。若此者,几不足以言群,愈不足以云社会矣”(严复,1981/1903:1)。一心追求富国强民的严复着重引进了当时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论思想,通过创造性的译介宣传自己以群治国、强国的主张。出于内心深沉的“经世”情怀,严复在译介斯宾塞之社会学思想时一方面强调其科学性,一方面亦注重其政治教化作用,以“修齐治平”为目标(姚纯安,2006)。“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罄香之极盛也”(王轼,1986:11)。“群”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当时知识精英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与之相伴随的“鼓民力、启民智、新民德”的启蒙径路也对后来的知识精英群体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在后文中我们还会述及严复思想对卢作孚的影响。
然而,正如论者所言,清末民初各种有关群学的主张存在同名异实的复杂情形(姚纯安,2006:12)。例如,丁乙指出,按谭嗣同的本意,万木草堂的群学并非西方的社会学,而是泛指西方民权政治学说(丁乙,1988)。虽然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一样谈“群”,但他们的“合群立会”之说更具有政治色彩(姚纯安,2003,2006:24)。维新派合群的方式是倡立“学会”,这是一种知识分子讲求学问、议论政事的自发组织。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序》中说,“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尝考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梁启超则在《论学会》中进一步发展出“商群”的讲法:“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梁启超,2007/1896)也即,要使整个国家的“群力”凝聚,议院是最好的办法;要将企业界联合起来,公司是最好的办法;要把士绅联合起来,学会是最好的办法(张灏,2014:59)。在这里,公司作为(士绅)自愿结成的经济团体,其意义第一次被与“群”联系起来。而公司与议院这两种群体,仍需以士人群体,即学会为基础。“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二者之母也。”(梁启超,2007/1896)同时,梁启超指出,“群”要真正建立起来,需要以利他主义的“群德”为基础。“(吾中国)然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梁启超,1985;转引自李培林,2008:40)道德因素在梁启超这里得到了强调,成为群得以建立的要件。
正如论者所言,梁启超尽管尊康南海为师且明显受到谭嗣同有关“仁”的道德思想影响,但也对严复所译介的社会达尔文式的“群”的概念表现出亲近和承接性。“梁对宇宙和社会有趋于群体整合和团结的‘群’的认识观点,浸透着一些达尔文式的概念、思想和隐喻,这极有可能是因为严复的媒介作用。梁在论‘群’的论文开头即承认严复的影响”(张灏,2014:54):“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梁启超论及“群力”时,将“群”视为一个宇宙论的原则,合群原则被设想为主宰宇宙间万物存亡的自然界本质规律(张灏,2014:53):“夫群者,万物之公性也。”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出发,合群原则主导着万事万物的生存竞争。梁启超进而提出了体现整合能力的“群力”概念,“群之力”的大小决定着各民族的生存竞争结果。“有能群者,必有不能群者。有群之力甚大者,必有群之力甚轻者,则不能群者必为能群者所摧坏,力轻者必为力大者所兼并”(梁启超,1988:31)。
政治家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离不开现代的政党组织,但他同样明白也“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要结成大团体,先要有小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宗族团体。孙中山(1986/1924)指出,宗族作为中国人国民和国家之间的“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可以紧密联系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相比外国人只是个人和国家的联系反而来得好。因此需要以宗族为单位,改良其中的组织,以恢复国族。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来看,传统的秘密会社所蕴藏的组织力量也给了革命事业相当大的助力。
与孙中山相似,黄遵宪提出的合群方案也是贯通中西,他提出“讲求合群之道,当用族制相维相系之情,会党相友相助之法,再参以西人群学以及伦理学之公理,生计学之两利,政治学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开民气昌,然后可以进以民权之说”(黄遵宪,1903;转引自姚纯安,2006:212),他认为建立现代的民主社会需结合传统社会的家族、会党等组织资源,再辅以西方的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理论的传播,提升“民”的素质。
以上诸位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在中西对比中意识到了中国的积弱根由在于缺乏集团的力量,他们提出的合群之道要么试图盘活传统社会的组织资源(家族、会党),要么则试图借力于西方的现代组织形式(政党、学会、公司)。要言之,都是要强化社会的组织。
这些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认识与合群之道的设想由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派转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农村社会实验,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是村治派的梁漱溟。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散漫、消极、无力,是因为不像西方人那样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中国人从来缺乏团体生活,处处像是化整为零的样子”(梁漱溟,2006:47),“中国社会病在散漫,救之之道,在于团结组织……结合团体是分子对团体的一种‘向心力’,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正在此”。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的这种局面,其途径就是建立新的乡村组织(梁漱溟,2006;李培林、渠敬东,2009)。他在河南与山东所做的乡村建设则是从办乡学村学开始,改造传统的乡约村约,以建立政教一体的乡村组织。他希望“从乡村中培养新组织构造的基芽”(梁漱溟,2006)。
费孝通对中西社会格局的判断与梁漱溟很近似,他同意乡土中国社会缺乏现代西洋的界限分明的团体格局。在他看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而且这个社会关系的网络界限并不分明,富于伸缩性。费孝通还进一步指出,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与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的差别引发了不同的道德观念,传统社会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缺乏基于个人和团体关系的普遍的道德要素(费孝通,1998:24—40)。
上文对清末民国时期知识界对“群/社会”的讨论以及培育群力的主张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与评述,意在勾勒卢作孚建设“现代集团生活”方案的思想与历史环境。由此不难看出,卢作孚的方案也从属于这一社会组织建设的基本脉络。他与其他知识精英一样,面对的都是一个传统的士绅阶层式微、国家与个人缺乏中介、社会缺乏整合的局面。要实现富国强国、抵御外侮的理想,从社会组织形态上说首先要增强内部的组织性,将个人的力量凝聚到组织上来。与梁漱溟等人在乡村重建组织相比,卢作孚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将组织建在城市中,在现代企业里,这是一项史无前例、从无到有的工作,“建设新的集团生活在一点没有新的集团生活的环境当中,最是困难的工作”(卢作孚,1990/1934:344)。不过,唯其困难之大,才可以显出其决心之坚,也更让这段历史经验更富有开创性的价值。
具体来说,结合卢作孚本人的思想发展轨迹和几次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实践,本研究关心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卢作孚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判断是怎样的?他的认识源于何处?
第二,如果卢作孚的判断和时贤无异,为何他又特别选择在城市、在企业中去开展集团建设?
(二)职业团体的研究传统
在对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学界理论主张进行简单回顾之后,让我们把视野投向社会学的学科话语。社会学正是伴随着近代工商社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对于讨论民生公司这样的现代企业而言,社会学可以提供丰富的学术话语资源,其中之一便是历史悠久的对于职业团体的研究传统。
社会学家们对职业团体的研究兴趣并非在于它自身,他们更关心的是现代社会中职业团体对于整个社会的整合、规范功能。从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其附带的伦理价值被打破,现代人陷入了方向迷失的困境,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涂尔干所讨论的失范,都是对现代人这种游离无依、无所适从的状况的经典把握。因此,在整合社会的目的引导下,社会学家转向了现代社会的组织,他们希望其为现代社会的整合、个体身份及其意义提供来源。在涂尔干看来,要消除现代经济生活中法律和道德失范的状态,要治疗利己主义自杀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弊病,需要依赖“同类劳动者、履行同样职责的合作者联合起来的职业团体或行会”(涂尔干,2000),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职业群体才是最广泛的初级群体,和国家等政治团体相比,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最直接、最广泛和最持久的道德生活环境(谢立中,2005:135)。借助职业团体这样一个次级群体组织,政府和个人也得以连接起来。从涂尔干之后,巴纳德(Bernard,1938)、尾内(Ouchi,1981)、彼得和沃特曼(Peter & Waterman,1982)延续了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参见斯格特,2002:311)。
具体到中国的经验,民国时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妙峰山》中留下了各个职业团体集体上山进香的生动记载(参见全汉升,2007/1934),而全汉升的(2007/1934)《中国行会制度史》则成了中国社会学界研究职业团体的发轫之作。他区别了依赖技术的手工业行会(手工帮)、依赖资本的商业行会与依靠体力的苦力帮。尤其是他对苦力帮的研究,此前一直为学界所忽略(参见李培林等,2009)。民国时期中国开始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工会、公会、行业协会等职业团体,从职业团体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当今的学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选择的是国家法团主义[4]的道路(魏文享,2004;裴宜理,2001:147)。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起开始训政过程,提出民众训练计划以及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对职业团体进行重新组织,讨论职业团体的政治代表性问题(魏文享,2011)。从两岸学者整理出版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尤其在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着力于人民团体的登记和“积极调整”,务求“居指导地位”,有关机关定期对各社会组织尤其是各地工会和公会加以统计,对于一些特种行业,则直接“协助组织工会”(秦效仪,1983;李文海,2009)。
1949年之后,在城市里普遍建立起来的“单位制”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国家对城市社会的控制,以职业团结为基础的单位成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所有城市社会的成员生老病死都在单位里完成(参见路风,1989;李汉林,1993,2008;李汉林、渠敬东,2002),单位成了“基本的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王沪宁,1995,转引自田毅鹏、漆思,2005:3)。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由魏昂德所开创的单位研究成为职业团体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魏昂德虽然没有使用“单位”这个字眼,但他通过对内地国有企业的研究提出了一种他称为“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的组织类型。在魏昂德看来,这种组织结构的主要特征在于“制度性的依附”(organized dependence),即工人在经济上依附企业、在政治上依附党政领导以及在个人关系上直接依附车间领导,从而形成制度化的“庇护网络”(华尔德,1996)。李猛等(1996)将魏昂德的工业权力研究进一步推进,对所谓“领导”这一概念加以细分讨论,指出领导并非意见一致的行动整体,派系正是基于其间的分歧而产生的一种纵向关系网络。“(单位中的)权力基础实际上是一种纵向关系网络。这个网络以单位内某一级别的某个官员为枢纽,呈分散状上下延伸出去。而在同一级别内,竞争使官员往往组合成几个分裂的单位。这样就形成了几个上下延伸、平行断裂的关系网络,我们将其称为派系结构。”李猛等人在单位中所看到的纵向的派系群体撬开了理想类型中的科层结构,指出了单位的非均质性以及这种“庞大的超级理性体制的裂痕”下的“自由空间”(渠敬东等,2015),为将情感联结、价值认同、道德约束等非理性因素纳入以前被视为超级理性体制的单位创造了可能。
如果说李猛等关注的是单位中的断裂和缝隙,那么王星等人对师徒制的讨论则将职业团体之内的职业身份形成机制和更具纽带作用的团结机制带入了学界的视野(王星,2009,2014;渠敬东等,2015)。
对于单位制的历史起源,现有文献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是路风(1993)的“供给制起源说”和卞历南(2011)的“抗战制度变迁说”。
1993年,路风发表了《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细致地分析了单位体制的历史成因,他认为单位制起源于革命根据地长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单位供给制传统。在根据地斗争时期,为了应对资源紧张,保证供给,党的革命队伍中的个体必须紧紧依附组织。在党获得了全国政权之后,为了实现对全社会有效动员,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配置,党的权威经过了一个向各基层组织贯彻、延伸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单位制这种特殊组织形式,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路风,1993)。
在路风之外,卞历南的考察也对单位制的历史起源提供了一种路径。他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的本土根源追溯到1949年以前。他指出,1949年以后国营企业三大界定性特征包括“官僚治理结构,具有鲜明特征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以及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卞历南,2011),这乃是抗战时期的制度变迁之结果。在日本大举侵华造成的全面危机之下,“为应付和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及其严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式及挑战”,国民政府开始调整其“思想模型”,不仅促成了中央计划官僚机构的建设、国民经济向兵器工业和重工业逐渐倾斜,在大量企业内迁而城市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许多企业还主动向员工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与福利,以期留住紧缺的劳动力,维持生产。
但无论是路风还是卞历南,都将单位制这种企业治理模式追溯到政治权威对劳动体制的绝对影响上。卞历南尤其强调从上到下的“思想模型”转变对相应的劳工政策、经济政策的整体影响。尽管卞历南的研究关注到了抗战之前已有若干民营企业开始在企业内向员工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的实践,但对于为何开始实践这一劳动关系体制是在抗战开始之前而不是之后、为何其最初出现于民营企业而非国营企业这一不符合其“冲突-反应”解释框架的历史经验事实,却并未过多着墨。[5]究其原因,卞历南可能过于强调官方政策指令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而忽略了对这些政策条令赖以运行的实在的民情基础的考察。
有学者并不同意仅将单位制度概括为控制与整合的权威制度的一部分。例如张静采取了法团主义式的问题视角,通过对企业职代会的案例研究指出,单位不仅代表了国家的控制力量,还有社会利益组织化传输的一面,它一方面是控制性的国家行政(设在基层)的组织,另一方面又是具有利益组织化及传输作用的(准)政治性组织,而单位的这种“政行合一”的双重性质使它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众之间的中介体,从而有效地作用于城市社会的冲突处理,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结构稳定(张静,2001a:24—26)。张静提出的对单位制度在社会控制之外的组织化利益传输的一面对思考职业团体与国家之关系颇具启发意义。
在讨论职业团体与国家关系时,法团主义是一个常用范式。安戈、陈佩华、皮尔逊、张静等学者已尝试将法团主义的框架用于解释改革以后的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陈家建指出,在分析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时,法团主义是比多元主义更为适合的研究范式,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核心区别在于,国家与社会不是分立而是融合的。在他看来,当今中国无论是在中国的城市社会、农村社会还是基层政府组织中,都出现了许多法团化的组织形态。在城市社会中,经济精英千方百计与官员结盟,以此来保障自身利益。这种经济精英阶层没有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而是与政府合作形成了法团化的组织结构(陈家建,2010)。安戈和陈佩华指出,在重视集体忽视自我的儒家文化浸润下,东亚各国具有容纳组合式(即法团式)制度的文化背景。他们还明确提出,在关于西方经济的法团模式的探讨中,除了工会和政府,大工业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参与者。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韩国的经济发展是由一些大的企业集团,即“财阀”推动的,在一种国家法团式的制度中,政府监督、协调企业集团的活动(Unger & Chan,1995;安戈、陈佩华,2001)。郑南(2013)通过对丰田公司以及当前的丰田市(即所谓“企业城下町”)的研究,以地域法团主义的视角说明了丰田公司对地域社会的全面支配。总的来看,“处于战争年代的国家,以及那些既强调政府指导下的经济快速增长,又力图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国家,往往容易诉诸组合式政策”(安戈、陈佩华,2001)。改革以后的中国正是后一种状况。按照施密特的分类,根据国家对社会管制力度之强弱,法团主义下又可以区分出“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两种类型(张静,2001b)。顾昕等(2005)进一步指出,以过程性的视角来看,其实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之两类法团主义在数量有限性、非竞争性、等级化、功能分化、国家承认的特殊主义、代表地位的垄断性、国家对社团的控制等方面均有共同特征。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真正的区别在于形成这些特征的过程有所不同。在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中,其特征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力干预形成的,即通过种种行政化或者明文规定的方式,国家赋予某些社团特殊的地位,而对竞争性的社团则根本不给予合法地位。相反,在社会法团主义模式中,某些社团享有的特殊地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竞争性淘汰过程形成的。郑南(2013)曾尝试比较以丰田公司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对地域社会强大的影响力和中国单位在国家面前的脆弱,其实二者之间的差异正源于社会法团主义与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之别。就中国经验而言,无论是抗战时的统制经济还是单位制时期的计划经济,虽然人们也依赖公司/单位才能获得各种资源,但国家仍处于强有力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法团主义体制。而针对战争时期的中国,也开始有学者运用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来处理工会等职业团体(胡悦晗,2010)。本研究也拟以法团主义为框架、以民生公司这个企业集团为案例,对战时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
总括上述对职业团体的研究,我们认为从职业团体的角度来看,主要应关心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从民生公司内部看,民生公司是否真正实现了以职业整合人群的目的?
第二,从民生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是合作、依附还是对抗?
第三,民生公司与单位制所讲的“单位”有什么异同?换句话说,以民生公司为代表的企业集团实践与单位制是否存在联系?
(三)劳工研究传统[6]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企业内部,势必离不开对最核心的劳资关系的讨论。甲午战争后,由于近代工商业迅速发展,劳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加之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劳工问题”进入了社会分析家的视野,一批社会学者长期致力于社会调查与研究工作(具体研究成果参见田彤,2011;闻翔,2018)。这些学者从工人生活状况、劳工团体、劳动争议、劳动报酬、福利设施、劳工法规等方面进行细致调查与分析,以寻求改善工人生产与生活状况、缓和劳资关系的方法。当时热衷于开展劳工调查的不仅是学者,国民政府也十分重视劳工问题,工商部、实业部陆续出版了全国性的劳动年鉴,一些比较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纷纷开展劳动调查,统计劳动争议(详参田彤,2011)。尽管在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劳资矛盾不断发生,但强调劳资和谐发展仍是政府劳动部门以及学界的主流。以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为例,陈达考虑劳工问题不囿于劳资利益对立的思路,而更多地从社会着眼。他主张“他们(社会问题研究者)的态度应该公正不偏,他们的研究应该注重事实的分析,以批评的眼光,做积极的讨论”。他也正是从事实切入对劳工问题的解决,并不赞成中国的工界采取激进的劳工运动,而是提出了一个工界、雇主、社会、政府多方联合协商的思路。他将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统一起来,一方面强调劳工的生存竞争压力应当适当减轻,另一方面,劳工作为社会阶级之一也对社会有贡献成绩的义务。“要想社会有进步,工人们亦必须有些成绩才是”(陈达,1929;杨雅彬,2009)。
类似陈达这样的重视数据资料搜集的调查被费孝通视为仅仅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见闻的搜集”,费孝通主张的是社会学调查,或称为社区研究,“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费孝通,1946)。他在西南联大期间也主持了一项“云南工业发达中劳工问题研究计划”,留下来的作品就是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与田汝康的《内地女工》。
田汝康的《内地女工》(1946)是对昆明一家纺织厂女工展开访谈后形成的报告,其中提到女工们进厂常常不过是要躲避家庭纠纷。史国衡在对昆明一家国营工厂的调查中也发现,工人们到厂目的各不相同,他们或是躲避家庭,或是为役政所迫,真正抱着在现代工业中求发展的想法的人并不多(史国衡,1946)。工人的来源、身份参差不齐也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技术水平、出身籍贯都成了造成他们之间隔膜的根源。史国衡发现,只是安排集体生活不一定能培养群的情感,也可以成为互相矛盾的基础,生活习惯的不同也可以形成冲突。员工间最大的断裂出现在工人与职员之间,作者认为现代工厂中这一对立源于传统社会中君子/小人、劳心/劳力的身份划分。费孝通(1946)在《昆厂劳工》的“书后”中认为,要解决现代工厂中这种分工而不合作的病象需要让组织中一切参加的人产生高度的契洽精神,而如何达到这一点呢?在当时西方人际关系学派的影响下,费孝通也提出要重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因此,“要使得工人效率提高,最好是使工人们把工厂看成是他们所关心的生活团体”(费孝通,1946:219)。
1949年以后,国内的劳工研究多采取阶级的框架,而海外中国研究者在对民国劳工史的研究中则试图逆着中国工人运动史的阶级对立的研究传统来提出问题,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性与整体性命题提出了质疑,他们对工厂、工人群体乃至工人家庭生活、工人与其他阶级之关系细致入微的经验研究弥补了国内惯常的仅以“阶级”视角观察工人群体、工人运动的不足。1980年代,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在天津、韩起澜(Emily Honig)在上海所做的工人研究是海外中国研究中著名的劳工史研究姐妹篇(Hershatter,1986;洪尼格,2011)。韩起澜在对民国期间上海棉纱厂女工的研究中发现,女工在地缘基础上持续分化,地方主义、殖民主义、青帮都成为阻碍她们团结一致和阶级意识产生的力量(洪尼格,2011);贺萧在对更为分散的天津劳工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跨阶级的联合的重要性(Hershatter,1986)。这与裴宜理《上海罢工》(2001)中所得到的工人阶级复杂分化的结论不谋而合。《上海罢工》挑战了以前劳工史研究中工人阶级的高度团结才能铸就阶级行动的假设,指出各种籍贯、产业、技术类别不同的工人阶级由于其历史和身份不同,拥有不同的利益,但工人阶级的复杂性并不影响他们的斗争性,除去阶级以外的其他各种认同也可能构筑起同仇敌忾的凝聚力并争取其团体的利益。研究北京工人政治的斯特兰德也呼应了这一结论,“现代的工人组织也只是工人们用于保护与增进自己利益的一个组织而已——从这个方面来说,纵向的动员和横向的动员至少是一样重要”(转引自Hershatter,1986:5)。
前文已经述及魏昂德对改革前的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华尔德,1996),他将工人与工厂领导之间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的依附-庇护关系归结为共产主义的新传统,因为这种垂直的效忠关系是个人化的、非正式的,甚至客观上在工人中造成了分裂效果,他的这一分析也被视为在“非阶级的分析方向上进了一步”(张静,2001a:15)。不过,魏昂德将工人与工厂间依附关系建立的起点放到革命之后的论断却建立在了对历史材料(尤其是对贺萧的天津工人研究)的误读上。魏昂德在谈及中国1920到1940年代的劳工关系时,认为基本上工人与工厂间没有联系,一切都依靠包工头(华尔德,1996:37)。但与魏昂德同一时代的美国学者贺萧就指出,至少在天津棉纺织工厂中,1930年代初产业界就兴起了取消工头制的风潮,而且在国营企业中建设提供各种福利设施的工人社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战后则更是如此。这些福利设施包括宿舍、食堂、诊所、子弟学校、消费合作社、浴室、运动场,而且产假、工伤保险、丧葬补助乃至剧社、乐队、英语课堂无所不包(Hershatter,1986:165)。天津市社会局留下的天津各业调查资料支持了贺萧的这一说法(吴瓯,1931a,1931b,1932;吴瓯等,1931)。实际上,更早期的劳工调查就提到了新工业的工人们所享受的福利设施:“国内有许多新工业,现在都为工人预备寄宿舍,只要工人们愿意略微出些房租,无论他们是已婚的或未婚的,都可以分别居住,如唐山开滦矿务局的工人宿舍,设备比较良善。又国内有许多工业雇主在工作场所替工人们预备食堂,如南通大生纱厂;或预备浴所,如上海丰田纱厂。除此以外,所有工人们的娱乐机会与设备,现在也渐普通,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同人俱乐部。”(陈达,1929:491)尽管魏昂德对革命后工厂与国家间的依附-控制关系的总体判断没问题,但对革命前的历史材料掌握得不够细致全面,这使他无意中失去了探索另一种解释路径的可能。
总的来看,已有的这些劳工研究作品,尤其是工厂民族志,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材料和经典的写作范本,更重要的是,它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领域和问题意识。如果说前述职业团体的研究传统关注的核心在更为宏观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那么劳工研究的传统则聚焦于更为具体的工厂、工人群体,它们以关注劳工为核心,其特点都可概括为对企业内部人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把握。那么,结合研究主旨,从劳工研究的传统出发,我们关心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民生公司内部是否有按阶层身份划分阵营、认同分离的现象?
第二,如果对上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阶层利益的冲突在何种程度上存在?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劳资关系得以融洽?
第三,公司里是否存在其他的劳工团结的形式?如果的确存在,它的作用是增进劳工群体的团结还是导致其分化?
(四)对卢作孚及民生公司的已有研究概述
对卢作孚本人的研究其实不在少数,除去传记作品以外,近年来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乃至美学领域,卢作孚研究都多有推进。西南师范大学(已于2005年合并为西南大学)是卢作孚研究的重镇,其卢作孚研究中心近年来多次主办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在2004年结集出版的论文集中可以看到与会学者们的研究关注点多落在乡村现代化建设、民众教育与职工教育等方面。其中比较独特的一篇文章是张瑾教授对北碚模式的研究,她指出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乃至重庆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民生公司的关联。自重庆开埠以来,长江航道一直是“下江商人”与重庆贸易往来的黄金水道,而民生公司的客运服务使它成为沟通重庆和外界的桥梁(张瑾,2004)。换言之,民生公司始终处在相对封闭的四川和下江文明交汇沟通的潮头。这一研究为我们理解民生公司制度创新的来源提供了一个背景。
此外,严云强(2004)专文讨论了卢作孚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思想。他敏锐地指出,卢作孚要建设的“现代集团生活”,其实质是“事业中心论”。此前,凌耀伦教授在一篇综述卢作孚研究的文章中指出,卢作孚想要建立的现代集团生活从属于一个虽有私有制但无阶级对立的社会,这是“一种经过‘改造’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包含着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凌耀伦,2000)。
西南大学的吴洪成、郭丽平(2006)等研究者的专著《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的事业与思想》系统地梳理了卢作孚毕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尤其在“公司学校化实验”中,对民生公司所开展的职工教育进行了总结(吴洪成、郭丽平,2006:191—205),特别指出卢作孚的职工教育目的是职工、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但最终其落脚点仍定位在为社会服务的层面(吴洪成、郭丽平,2006:265—267)。在与同样兼具实业家与教育家身份的张謇对比时,该文作者认为卢作孚更好地将职业教育和事业融为了一体,民生公司学校化的实验让他的教育思想和现实事业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吴洪成、郭丽平,2006:300—301)。
在众多研究者中,赵晓铃是为数不多的关注卢作孚“兼善”思想的研究者之一。她通过研究民生公司分散化的股权分配、优厚的职工福利待遇和新村式的职工集体生活指出,民生公司一开始就朝着公有化的道路前进(赵晓铃,2000)。在近期的新作中,赵晓铃以民生公司档案为材料,真实展现了1945年以后民生公司如何在内外交困中走向劳资矛盾激化,最后卢作孚悲情谢幕的过程(赵晓铃,2010)。其中对在民生公司发动阶级斗争之难的描述从侧面反映出了公司集团生活建设的效果。以1950年“西崽”要求改善待遇的事件为例,我们可以见到原来职业团体的团结如何被主流的阶级斗争的话语日渐分割(赵晓铃,2010:97—99)。
在对民生公司历史的研究中,以“中国水运史丛书”之《民生公司史》(凌耀伦,1990)最为翔实可信。该书由经济学人担纲主编,尤为注重挖掘经济史料,不仅查阅了长航公司保存完整的民生公司原始档案,还走访了民生老职工数百人次。可贵的是,该书不但注重从民生公司自身的经营管理角度进行总结,还将民生公司置于时代经济背景之中,与同一时期的其余企业进行了多处对比,因此尤富参考价值。
西南大学刘重来教授关注卢作孚对于北碚的乡村建设有年,2007年推出《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一书,挖掘卢作孚在北碚的乡村建设成就,指出1920—1940年代末卢作孚及其胞弟卢子英等人在嘉陵江三峡地区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同时,该书也阐明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能取得与众不同的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得到了民生公司的大力支持(刘重来,2007)。与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模式不同的是,北碚的乡村建设解决了靠外部输血的问题,通过民生公司以投资形式参与或主持峡区建设,以工辅农;同时民生公司也获得了稳定低廉的煤矿供应、环境良好的学习培训基地和训练有素的建设人才,实现了互利共赢。可以看到,北碚和民生公司作为卢作孚现代集团生活建设的两个试验场,两者并非互不相干,而是通过卢作孚的整体的社会“群力”培育规划相联系。
在当代史学界城市史、新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风潮推动下,一些研究四川、重庆社会的海外史学家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张瑾,2003),其中以罗安妮(Anne Reinhart)对中国航业的研究影响最大,她的研究将中国航业放在半殖民地的背景之下,对长江流域社会生活展开生动写照,涉及民生公司整合川江航运、废除买办制度、茶房招聘制度等微观层面。她以轮船上的社会空间为譬喻,关照长江上的航业企业如何在与外国资本的角力中开创空间,发展民族资本。不过,由于该研究侧重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航业如何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企业内部的集团建设及其与国家关系并未着力分析。而且其研究以1937年为下限,未能涉及抗战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Reinhart,2002)。
2016年,编辑收录民生公司历年来各界人士演讲的《民生公司演讲集》问世(项锦熙,2016),该书系1932年到1946年公司朝会上的演讲实录,主讲人包括黄炎培、翁文灏、马寅初、张伯苓、梁漱溟等各界名流。翻阅其中的演讲内容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上民生公司开放的精神面貌提供了一个深入的窗口。可以看到,尽管重庆偏处西南一隅,但随着政府机关、企业、学校不断西迁入蜀,全国人才荟萃于巴渝之地,各种思潮亦汇聚在民生公司小小的演讲台上。战时的重庆虽对外交通相对不畅,在精神上却绝非孤岛。仅就开放眼界关注世界先进文化与潮流而言,留德博士王希城讲德意志之民族性如何勤奋雅洁讲究公德,留日的川大教授介绍日船服务如何殷勤规范,在耶鲁学成归国后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李登辉则介绍了美国福特公司如何通过劳资合作获得事业的成功,并对中国的实业发展提出期望(项锦熙,2016:27、124、391)。
最后要提及的是由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室主办的刊物《卢作孚研究》。该刊虽是内部同人刊物,但内容丰富、编排严谨,反映了卢作孚研究的最新状况,文献出版、专题论文、历史随笔、史料钩沉等无所不包,是卢作孚及相关研究的同人了解研究进展和最新前沿成果的最佳平台。
纵观已有的卢作孚与民生公司研究成果,篇数虽不少,却多介绍、整理,少分析、挖掘。从已发表的文献来看,在描述性的作品之外,目前主要的研究突破方向集中于卢作孚在北碚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和职业教育上的贡献与经验,从社会学入手探究民生公司现代集团建设的组织研究几乎阙如。因此,这也就成了本研究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