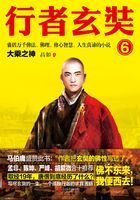
第1章 求学那烂陀
般若羯罗帮助玄奘将简单的行李搬进戒日王院,二人穿过庄严豪华的塔寺、精舍、僧坊等建筑,一直上到第四重宝阁。
“师兄你知道吗?我们的食宿可都是觉贤长老亲自安排的。”般若羯罗边走边介绍道,“这戒日王院可不是普通的僧舍,寺中很多长老都住在这里。你想想看,有几个学僧能够享受到与长老同住的殊荣呢?羯罗住在第二重,已是受宠若惊。觉贤长老就住在第三重宝阁,只比我高一层,师兄居然还在他的楼上!”
刚说到这里,却发觉身后的脚步声停了下来,玄奘略有不安地说道:“我只是一介求法的学僧,怎么能够居于大德之上?这万万不可!”
说着,转身就要离开。
般若羯罗一把拉住他道:“师兄还是听从安排吧,那烂陀寺自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我等前来求法的僧侣,何必违背?”
这话说得有理,玄奘心中虽然仍有隐隐的不安,却又无可奈何。
第四重宝阁是两个套间,一个由学僧使用,一个由侍者使用。
玄奘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发现里面虽不算大,一切生活和学习用品却是应有尽有。并且独门独户,十分清净。
般若羯罗上前帮他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立即飘入房间。他指着南边不远处的木制精舍道:“师兄请看,那里便是护法菩萨的故居。”
玄奘心中一凛,护法菩萨乃是印度佛教十大论师之一,那烂陀寺前任寺主,又是正法藏戒贤尊者的师父,想不到自己以一个初来乍到的学僧的身份,竟然得以与圣者毗邻。
望着那座被大片郁金香包围的美丽精舍,玄奘似乎明白了戒贤尊者和那烂陀寺对自己的期许和良苦用心……
七天后,寺中又给玄奘配备了一个名叫卢达罗耶的婆罗门净人和一头名叫诃利的大青象。
象是印度人最喜爱的动物,有实力的国王训练大量象军作战,普通印度人则用象来做更多的事情。例如用象鼻子卷着扫帚扫地、搬运柴草;农民下地干活,用它驮载一家老小及工具;有的人家还用大象来照看孩子。
诃利长着一颗圆而大的脑袋,皮肤坚厚,非常聪明,性情也极为温顺憨厚,惹人喜爱。在这之前,玄奘很难想象,那么庞大的动物,竟有如此温顺的脾气。
更难想象的是诃利那条长而柔韧的鼻子,前端竟长有类似手指的突起,异常灵活。玄奘原本以为,它只能用长鼻子卷起石头、木料等粗笨的物体,却不承想,它竟然也能捡拾像花生那样细小的食物,更能轻松自如地剥芭蕉皮,着实令他大开眼界。
领取了诃利之后,玄奘坐在象背上回自己居住的戒日王院,他没有指挥大象的经验,更不知道该如何让大象转弯,于是诃利便抄了近路,径直朝寺中央的大湖中走了过去。
这里是那烂陀寺学僧们平常休闲和纳凉的地方,最深处仅有两人高。诃利显然很喜欢水,玄奘也不介意,反正他现在已经会凫水了,炎热的天气从湖中经过只会让他感觉到凉爽。
诃利越走越深,湖底的淤泥被它的四蹄翻了上来,弄得玄奘满身都是。到达湖中央时,它整个后背都没入水中,长长的鼻子高举着,伸出水面呼吸。玄奘可没这个能耐,只好站在大象背上,抱住它的鼻子,防止自己摔下去。
湖边偶尔有人经过,玄奘心中暗想,我现在这个样子一定很可笑吧?
但是没有人笑话他,事实上,这是那些青年学僧平常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
净人卢达罗耶取了玄奘的东西追了过来,见诃利背着玄奘下水,也不介意,径直跑到对岸去等他们,般若羯罗也在那里。
诃利终于上岸了,卢达罗耶赶紧过来,要把玄奘从象背上扶下来。
玄奘苦笑道:“我浑身都是泥,当心沾你一身。还是赶紧回去找清水洗个澡吧,顺便也给诃利洗一洗。”
卢达罗耶笑道:“不用,诃利自己会洗。我准备也来沾点儿光。”
玄奘不明白他的意思,好在诃利很快就以自己的行动做出了解释,只见它把长长的鼻子伸向后背,一股水流喷洒出来,冲刷着身上厚厚的淤泥,也冲了玄奘和卢达罗耶一身。
“怎么样法师,很舒服吧?”卢达罗耶开心地问道。
玄奘可一点儿都没觉得有多舒服,象鼻子里喷出来的水是热的,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他甚至觉得有点儿黏。他现在头上、脸上、身上都是泥水,只想远远地躲开,又担心这么做会让诃利不痛快,一时竟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般若羯罗没过来和他们一起冲象鼻澡,只在一旁看着玄奘的狼狈相,不停地笑。
对这家伙的幸灾乐祸,玄奘感觉不平,正想说点什么,突然大片的沙子从天而降,落了他满头满身!他忍不住“哎哟”一声叫了出来,这才发现,诃利居然在湖边吸起了沙子,喷在自己和主人的身上。
机灵的卢达罗耶赶紧躲开,般若羯罗则指着玄奘,笑得捂着肚子。
玄奘拍了拍头上的沙子,也释然地笑了。身为一个高僧,被一头大象弄得如此狼狈,倒也是一桩趣事。
回到戒日王院洗了个澡,玄奘便领着诃利去见银踪。
身为印度的圣物,诃利在“小不点儿”银踪面前尽情展现了自己的高傲;而银踪也对这个新来的“傻大个”表示了充分的鄙视和不屑。面对此情此景,玄奘实在不放心把它们两个养在一起,只好又将它们分开了。
对于那烂陀寺给予自己的礼遇,玄奘没有做太多的谦让。一来,那烂陀寺占地四十八里,拥有象骑确实可以更方便地在寺中走动;二来,他知道自己肩上承担的使命,物质和生活上的享受对他来说不值一提,他所关注的,是即将到来的艰苦而充实的求学之路。
玄奘终究是幸运的,他到达那烂陀寺的时候,虽然印度整体的佛教环境正在衰落,那烂陀寺却依旧保持着全盛时期的规模。早些年,寺内主要还是以大乘中观、瑜伽行派为主,兼讲十八部派学说;后来又增加了吠陀、五明、天文、术数等学科;再后来,各种门类的学科如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医学、数学、地理学等,也都在僧侣们的研习之列,哪怕是裸身、涂灰等外道,都可在此找到一席之地。那烂陀寺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包容了这一切,以至于很多非佛教徒也到这里来学习,数量加起来竟然比僧人还多!
严谨开放的学风使得这座佛教寺院逐渐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彻底成为了五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
玄奘到达时,寺内有宝彩、宝海、宝洋三大藏书殿,藏书超过九百万夹,常住僧人数千,加上慕名前来学习的外客婆罗门道俗,总人数超过万人!
这一天,是玄奘到达那烂陀寺的第九天。
这一天,那烂陀寺寺主,已经一百零六岁的正法藏戒贤大师,在经过了多年沉寂之后,决定为一位来自东方的学生亲自授课。
消息传出,万众瞩目。
一大早,那烂陀寺法鼓齐鸣,钟声响彻云霄,上万僧俗云集于大讲堂前,一时场面空前壮观。
戒贤尊者环顾全场,朗声说道:“在所有的礼物中,真理的传送最为珍贵;在所有的味道中,真理的味道最为殊胜;在所有的快乐中,真理的喜悦最为持久。祓除贪欲,便可以征服所有的苦恼!”
这番充满激情的话语一直撞击到了玄奘的心灵深处,使他禁不住热泪盈眶。现场的每一个人也都打起精神,准备用心去聆听尊者的教诲。
谁知就在此时,场外突然喧哗起来,众人惊异地回头,却见一位身着白衣的婆罗门在法堂门前忽而悲泣,忽而言笑,引得全场侧目。
莫非是有外道前来捣乱吗?戒贤忍不住看了玄奘一眼,却见玄奘只是静静地坐着,脸上并无疑惑之色,更无烦躁之感,尊者心中不禁慨叹,这个年轻的求法僧确实修为不凡!
这时,觉贤长老已派人前去查问缘由,很快便将那白衣男子带到跟前。
“居士是从哪里来的?”觉贤长老平静地问道,“如果是来辩论的,就应该立论递帖,不该在这庄严的法会上捣乱。”
“弟子不敢捣乱。”那人伏地叩首道,“弟子是东印度人,名叫皮特耶,曾经在布磔伽山观自在菩萨像前发愿,是菩萨要弟子到这里来的。”
“居士发的什么愿?”觉贤长老问道。
“弟子发愿为王。”
周围已经有人小声地笑了起来,在这些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看来,这个愿望实在可笑得很。
觉贤长老也觉得有趣:“这里是那烂陀寺,修行之地,如何能满足居士的这个愿望?”
“是。”皮特耶道,“所以弟子受到了菩萨的呵斥。”
“居士的意思是说,菩萨现身了吗?”
“是的,菩萨对弟子说:你勿作此愿!速往那烂陀寺,戒贤尊者要为东土客僧开讲《瑜伽师地论》[1],汝闻法后当得见佛,何用做王!”
原来他竟然是得到了菩萨的开示,才到这里来的。会场的人们都不禁面面相觑,面露惊奇之色。要知道,不是每个人的许愿都可以看到菩萨现身的。
或许,菩萨是发现此人与佛门的因缘到了吧。
皮特耶接着说道:“弟子得到开示后,一刻也不敢怠慢,立刻赶往那烂陀寺。果然看到戒贤尊者大开讲坛,将为东土法师开讲《瑜伽师地论》,竟与菩萨所言一模一样!只恨弟子非本寺之人,无法进入会场,是以心中悲喜交集,一时间情不自禁,搅乱了会场,还望诸位大师恕罪。”
原来如此!得知此事原委,觉贤长老立即叫人给这个婆罗门安排了听经位置。
万众瞩目之下,戒贤尊者开始宣讲大乘瑜伽行派的主要经典——《瑜伽师地论》。
宝海阁是那烂陀寺三大宝阁之一,里面收藏着般若、中观、瑜伽、唯识学等大乘经典。可以说,在玄奘求学那烂陀寺的五年间,这里是他到的最多的地方了。
阁中所有经函都装在宝箧之中,然后分门别类,存放于各层书柜之上。
“这三座宝阁可算是娑婆世界佛教典籍最集中的地方了,历次结集的三藏经典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看守宝海阁的僧人这番自豪的介绍让玄奘深信不疑,他自认为还算是个见多识广之人,但在第一次进入宝海阁时,还是被这里面的空间之大和藏书之多深深震撼了!
之后的日子里,玄奘几乎将讲筵之外的全部时间都泡在了三座宝阁之中,每日里胁不沾席,甚至连用斋的时间都很短,只在阁中端坐阅经。
中印度天气酷热,他却觉得内心无比清凉,仿佛坐在一朵清净的莲花上。
在西域、中亚和北印度常见的苍蝇和蚊虫,这里也都不见影踪,原因是这里的热季找不到阴凉之地,蚊虫们全都被酷热杀死了,这倒使得玄奘可以专心阅藏而不受任何干扰。
由于去的次数多了,他与看守藏经阁的僧人和猫儿们相交甚厚。那些小猫经常会在他读经的时候凑过来,有的卧于他的腿上,有的趴在他的身旁;守经人每天都会将他常用的灯台擦拭干净,再在旁边放上一碗凉茶,而在他读完一卷喝上一口茶的间隙,他们便会兴致勃勃地给他讲述这三座宝阁的传说故事:
“那烂陀寺刚刚兴建之时,经常受到一些外道的滋扰。有一次,两个修持火光三昧的家伙来到寺门外挑衅,他们念动咒语,喷出炙热的烈焰,那烂陀寺顿时被包围在一片火海之中。”
玄奘这才恍然:“难怪宝阁附近的石壁上有被烧焦的痕迹呢。”
他对此倒并不介意,有着几百年历史的那烂陀寺,如果没有这些磨难,反倒不正常了。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磨难,而是那烂陀寺终于从磨难中走了出来,这才拥有了今天的辉煌,也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守经人见他听得认真,很是高兴,越发滔滔不绝起来:“不可思议的情景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法师你能相信吗?大火起来之后,从宝洋阁第九重宝阁的一部密续经函之中,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出大水,将大火熄灭!这才保存了宝洋阁的全部经典和宝海、宝彩阁的部分经典。”
玄奘心里一动:“密续经函?就是那部《胜乐金刚经》吧?”
守经人惊讶地说道:“法师连密教的经典都看,莫非是打算把这三座宝阁中的经典都装进脑子里吗?”
如果有可能的话,玄奘倒真希望是这样!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只能在阅读过后,将一些最重要的经典笔录下来。
“法师还想读什么经?我们帮你找!”这天,见玄奘刚刚整理完一部经典,一位守经人热情地说道,“正法藏有交代,那烂陀寺对玄奘法师完全开放!”
玄奘心里十分感动,他轻抚腿上的猫儿,随口问道:“有《首楞严经》吗?”
他倒不是急于看到这部久闻其名的经书,只是在这宝阁中也待了不少日子了,每天上上下下地不知转了多少圈,很多熟悉和不熟悉的经典以及婆罗门书都在书柜中看到过,唯独没有发现这部经,心中隐隐有些好奇。
守经人的脸上露出惊奇之色:“法师是从哪里听到这部经的?很多印度大德都没有听说过呢!”
“哦?”听了这话,玄奘心中的好奇更甚,“此经与我东土有缘,很多汉僧都知道的。有位德高望重的大师为让此经流布东土,曾在自己修行的山中设立拜经台,日日虔诚礼拜,历时十八年之久,始终未能得见,深以为憾。所以玄奘知道此经。”
两名守经人的眼睛立刻瞪圆了,愣愣地看着玄奘,显然是被他说的这不可思议的因缘给震撼到了。
“另外还有一位前辈,早玄奘二百多年来到印度,他曾在灵鹫山的石窟中见到过《首楞严经》,彻夜读诵,并将此事记录在他的笔记中。可惜玄奘无福,虽然也上过灵鹫山,却未曾见到此经。”
说到这里,玄奘的神情有些黯淡:“那烂陀寺没有这部经吗?”
守经人摇头道:“确实没有,听说这《首楞严经》整个印度只有一部,藏在戒日王的王宫里。”
玄奘很是奇怪:“戒日王?他藏经作甚?经书乃是佛门法宝,理应由寺院收藏。若是他虔诚信佛,在宫中保留一份,每日诵读,倒也是莫大的功德。只是这与寺院的收藏并不矛盾啊。再说那烂陀寺不是受戒日王供养的寺院吗?”
“话虽如此,但是摩揭陀的历代圣王都不允许寺院收藏此经。”守经人说到这里,凑近来,略带几分神秘地小声说道,“此事从帝日王时期就开始了,听说,这经中的法是有秘密的!”
“秘密?”玄奘不禁哑然失笑,“什么时候《首楞严经》也成秘密的了?好吧,玄奘是听说此经在内容上包含了显密性相,可是就算是秘密的,这宝阁中的密续经函难道还少吗?寺中僧侣不都可以随意翻阅?怎不见有圣王前来收缴?”
“这是不一样的。”守经人解释道,“密续经函只是密宗修行法门,对圣王的吸引力不是太大。至于那部《首楞严经》,里面可不仅仅是修行用的法门,听说还可以破魔的!”
“破魔?”
“是啊。”守经人道,“我们都没有读过此经,只是听说,此经从破魔起,至破魔终。那里面有一篇咒语,所在之地,邪魔皆怕。因而为历代圣王所珍视。他们将经夹藏于王宫之中,让它保佑摩揭陀国不被魔侵。但他们又不希望让此经去保佑别的国王,于是便下了严令,任何人都不得将此经外传。”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玄奘不禁皱起了眉头,“好好的佛经被用作这种用途,岂非好笑得很?玄奘倒也听说过此经为破魔宝典,但是你们知道魔在哪里吗?不在别处,就在每个人的心中。特别是修行人,很容易为魔所迷转。据我所知,这部《首楞严经》对末法时期的种种乱象,尽数说到,并且指出了对治之方。若有本经住世,则正法便可住持世间,佛弟子们修行也将有所依持,从而不受迷惑、不入岔道。这才是它真正的破魔之处,破的是人心之魔,而不是什么张牙舞爪的外魔。”
“也许法师说得有理。”守经人小声说道,“但是圣王的心思谁能猜得到呢?”
玄奘长叹一声道:“那些所谓的圣王,怀着独占的念头,阻止经文流通,心中怕是早已被魔占据,却不自知也。”
五月,正是中印度最热的季节。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烤得大地滚烫。空气似乎也变成了火,直叫人透不过气来。每一间屋子都大张着嘴巴,像水中的河马一样,在烈日下大口喘着粗气。
作为佛门圣地的那烂陀寺,同样被一团无形的火焰包围着,炙人的热浪从红砖地面上蒸腾而上,直扑脸颊。杧果树间盘旋着灼人的旋风,野草在酷热中无精打采地昏睡,塔影在阳光下斑斑驳驳,仿佛一下子又苍老了几百年。
这样的天气,就连寺院里正常的辩经活动也少了许多,在外面走动的多是那些忙碌的侍者。
卢达罗耶肩背一只藤筐,顺着戒日王院的楼梯登上第四重宝阁,热气蒸得他满脸通红,汗流浃背。
同往常一样,他看到玄奘正在窗口处伏案苦读,从宝海阁里借来的贝叶经全部堆放在屋子一角的桌案上,案旁有一只藤条筐,里面放着尚未吃完的瞻步罗果、供大人米以及各种香料。
“法师,今日的供养到了,放在哪里?”卢达罗耶卸下肩上的藤筐,环顾四周问道。
“这里放不下了。”玄奘头也不抬地说道,“你给般若羯罗法师送去吧。”
“小人刚才上阁时,经过般若羯罗法师的房间,本就直接送去的。可他辞谢说,法师昨日送给他的还没吃完呢。”
“哦。”玄奘放下了书,回过头来。
从进入那烂陀寺的第二年起,玄奘就跻身寺中大德的行列,后来更成为寺内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备受尊崇。那种摩揭陀国特有的,产量稀少、专供王族和顶尖学者享用的供大人米,如今竟成了他的主食。
他每日可以得到供大人米一升,还有数量更为稀少的瞻步罗果二十颗。另有槟榔子、豆蔻、龙脑香等香料,这些供养都由净人卢达罗耶帮他拿到僧舍。
玄奘每日习经,几乎废寝忘食,根本就吃不了这许多,加上他严守佛家“日中一食”的戒律,因此这些供养大都用来送人了。
“听说最近大德师子光正在寺中开讲《中百论》[2]。”玄奘沉吟道,“很多听经的僧俗常会误了斋食时间,正需要些果米补充,你送到他那里去吧。”
“法师……”卢达罗耶的脸色有些不好看,“还是别去招惹师子光长老吧。”
“怎么了?”玄奘奇道。
“小人听说,他讲的《中论》《百论》,是反对法相唯识之说的。”
玄奘不禁笑了起来:“难为你还知道这个,中观学派与瑜伽行派虽有些争执,但同属大乘佛法。咱们那烂陀寺学风宽厚,便是六师外道都可在此拥有一席之地,不同信仰的徒众们坐在一起听经习论,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何况同为佛门弟子?以前师子光长老讲说《中百论》的时候,玄奘还去听过呢,你不记得了吗?”
“小人记得。”卢达罗耶气呼呼地说道,“那长老话中带刺,不像个长老的样子!”
“那也只能说明他本性刚直,这是因习气引起的各人性格的不同,与正法的弘扬并无妨碍。你又何必在乎这个?”
“可是法师啊,这次师子光长老讲经与往常不同,小人听说,他不仅批驳瑜伽宗不合经义,还时时大骂瑜伽行者,矛头直指法师和正法藏呢。”
听了这话,玄奘不禁皱起了眉头。
在印度的大乘佛法中,中观学派与瑜伽行派各成一体,彼此争论不休已经有些年头了。
早在数百年前,中观学派的月称论师便在其所造的论书中,评析了瑜伽行派。月称认为,瑜伽行者的唯识说——“依他起”与“圆成实”有自相说,是不了义的,是为劣根机者所做的方便说法。这种说法还算客气,至少还承认唯识学说。到了婆毗呔伽即清辨论师的时候,则做得更加彻底,清辨在《中观心论注》里指名道姓地痛驳瑜伽宗义,很干脆地予以否定,不承认有阿赖耶识,不承认有自相和自相续,不承认有外境,不承认自证分。
总之,清辨论师认为,瑜伽学说不是什么不了义,而是根本就不合经义,应该彻底摒弃。
瑜伽行派的对策,则是为龙树菩萨的《中论》和提婆菩萨的《四百论》做注释,以此来评价中观学派,并以相对委婉的方式表达己意,这就是传说中的“空有之争”。
玄奘到达那烂陀时,寺中早已形成了两派对峙——正法藏戒贤是瑜伽行派护法的嫡传,而师子光长老则是中观清辨一派,玄奘也知他平素里常寻机批评瑜伽行派,甚至对正法藏也多有微辞。
在那烂陀寺学习的几年间,玄奘与这位性情刚直的长老极少交往,只听过他的几场讲筵,其中就包括《中百论》。虽然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也觉得在思维方面有所进益。师子光知道他是正法藏的得意门生,看到他来听经,总忍不住讥刺几句,令卢达罗耶十分恼火。玄奘对此却毫不在意,该听经的时候还是会去听的,他执着于知识本身,而不是知识持有者的身份。
好在师子光长老毕竟是寺中大德,虽然对瑜伽行派怀有偏见,讲经的时候总还会留有一些余地,并不像当年的婆毗呔伽论师那样赤膊上阵,指名道姓地公然指责。
如今,是什么使这位长老一改往日的隐晦,借讲经之际开始向瑜伽行派发难了呢?他的这一举动,会不会使那烂陀寺再起争端?玄奘对此深感忧虑。
“走吧,咱们一同去听听,顺便拜访一下师子光大师。”这种事情单靠坐在屋子里想是没用的,玄奘索性站起身来。
“法师是要去反驳他吗?”卢达罗耶眼睛一亮,有些兴奋地问道。
“不。”玄奘笑道,“只是去听经拜访。”
“法师您等着,我这就去牵象。”卢达罗耶立即转身出门。
骑在诃利宽广的背上,玄奘还在梳理着自己的思绪——
一般来说,治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重考据重辞章,这是中国传统经学与印度婆罗门教的路子;另一种重统体重大观,这是很多佛家宗派的路子。就玄奘个人而言,他是更主张“会宗”的统体观的,那就是,既重经典之原文,更重义理解读。不过相比较而言,他的思维方式更加偏重于宏观和义理。
然而印度僧侣的一些思维方式却让他有些不习惯,他们似乎更加固执,对于细节的探讨也更加地细微化,常因一些细节上的差异而分出派别,彼此对立,论争不休。
有一回,两个不同部派的僧侣,为了个极其微小的问题争论得很是激烈,谁也说不服谁,正好玄奘路过,便被拉去做裁决。对此,玄奘也只能无奈摇头:“此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在玄奘看来,只要自宗内部是圆融无碍的,修行与理论方面没有矛盾之处,佛教的任何法门都可以导向最终的觉悟,为一些细节争论实在是浪费时间。
可惜印度人大都认死理,不光部派佛教的徒众如此,大乘也一样。比如“中观”和“瑜伽”两派,明明都是大乘佛教,又都承认“空”,可在学理的方法论上,彼此对于“空”的定义却截然不同,中观学者认为,一切法无自性空,是究竟了义的;瑜伽行者则说,一切法无自性空,是不了义的。
在印度,大乘佛法原本就比不上部派佛教那么隆盛,偏偏内部还要争论不休,让人无奈。
其实何止是印度呢,玄奘忍不住想,自己之所以西行求法,除了求解圣典疑义外,主要还不是因为中原汉地亦有此论争吗?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印度之后,各种纷争不仅不见减少,反而更加激烈了。
“对了,法师您还记不记得皮特耶?”卢达罗耶牵着诃利,回身问道。
“皮特耶?是谁啊?”玄奘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一时没反应过来。
“法师您怎么忘了?就是五年前,在正法藏菩萨的法会上又哭又笑状似疯癫的那个家伙啊!”
玄奘终于想起来了:“是那个在菩萨面前发愿要当国王的婆罗门吗?记得当初,他听正法藏讲经时极为认真刻苦,为人又谦逊友善,是个很不错的道友,玄奘还曾向他请教过呢。如今好些日子不见,倒真是差点儿把他给忘了,他现在还在那烂陀寺吗?”
“早就不在了。”卢达罗耶笑道,“两年前就离开了,正法藏撤了讲筵之后离开的。”
“原来,已经这么久了……”玄奘喃喃地说道。
戒贤尊者亲自为他设讲筵,开讲《瑜伽师地论》的情形,恍惚就在昨日。还记得那时,讲堂内外一片寂静,数千人聚集在一起听讲,竟无半点杂音。只有正法藏苍老宏朗的声音,不分远近,清晰地传到每个人的耳中……
而方才听卢达罗耶说,此事已经过去五年了。
仔细想想,可不是吗?光是那部二十万颂的《瑜伽师地论》,戒贤尊者就整整讲了三遍!作为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著作,《瑜伽师地论》规模之大、体系之完备、组织之严密、说理之透彻,都与普通经书不同。戒贤尊者以百岁高龄,不辞辛苦,每日三讲,足足讲了十五个月,才将这部大论讲完一遍。
这之后,为摄受遗漏未明者,尊者又回过头来,从头至尾讲了两遍。
在那段重讲的日子里,玄奘依然每日前往导师处听习,随时向师尊质疑问难,并详为研究梵典,用他全部的心思和精力潜心钻研,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经论中的知识,直至能够洞达其辞,能清晰典雅地运用,并与自己先前所学融会贯通,心中才觉舒畅。
算下来这可就将近三年了,自从那年不辞而别地离开兄长,沿江出蜀,他还从未在一个地方待过这么长时间呢。
注释:
[1]“瑜伽”,汉泽相应,是智与境、行与理的契合;“瑜伽师”是指三乘行者次第修习瑜伽,获得成就的人,即瑜伽的大师们,相当于中国所说的禅师;“地”是层次或境界的意思。《瑜伽师地论》主要讲的是:修行人从凡夫修成佛道,总共需要经过的十七个层次,或十七种境界,因而又被称作《十七地论》。此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内含菩萨戒本、解深密经等内容,堪称佛教瑜伽行派和唯识宗的百科全书。
[2]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论》与提婆菩萨所著的《百论》,合称《中百论》。两书均为大乘空宗(即中观学派)的经典。